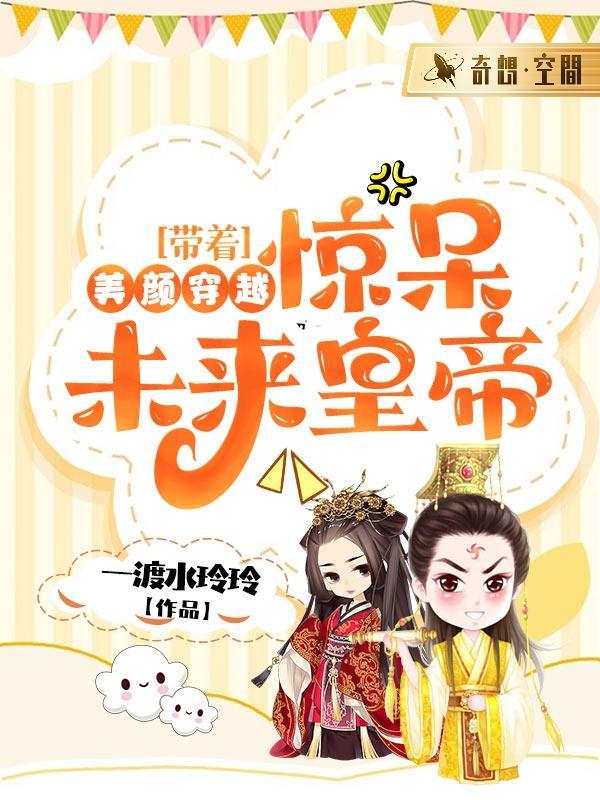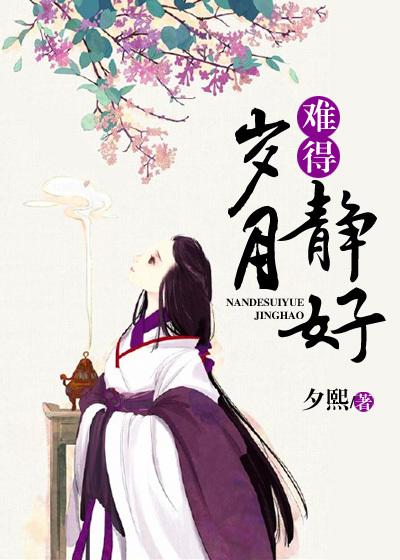书蛋文学>我真的是咸鱼[快穿] > 第26章(第2页)
第26章(第2页)
几位大臣刚进御书房就跪了一大半,重重磕了一个响头:“臣等请陛下遣使者与匈奴求和。”
“臣知陛下有大志,但求陛下为社稷计,忍一时之辱,保国祚延绵!”卢涵林跪直身子,他目光恳求,额头上红了一片,可想而知方才有多用力。
“攘外必先安内,请陛下下令南北大军回防,再治成王之罪。”
只是求和而已,前面几朝又不是没求和过,只可惜本朝没有适龄的公主。
但郡主还是有几个的。
大齐养了她们这么久,家国有危,如今正是她们舍身报国之时。
匈奴也好、回鹘也好,不就是想要粮食吗?大不了给他们,反正打战也要耗费军粮,就当是将这部分粮食节省下来。
也许会苦一苦百姓,但他们又有什么办法呢?天灾如此,天不佑大齐,人又能为之奈何?
颜慎缓缓跪下,平静却坚定道:“臣反对。”
这便又回到早朝时的争端了。
自异族有动静以来,早朝时总要吵上这么一架。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右相清高,右相不同意,那您倒是拿个主意出来啊?”卢涵林讽刺完,再度向沈永和请命:“臣绝无私心,请陛下明鉴,臣愿为使臣。”
出使从来就不是个好活,更何况这还是去求和,指不定百年之后留下一片骂名。
他是真心觉得求和更好,先舍弃点财富保河山安稳,拖延些时间,等把不安分的藩王料理完了才腾出手来处理外敌,有何不好?
“卢尚书怎么保证匈奴不会撕毁盟约?”颜慎寸步不让:“成王敢这样大胆,不就是觉得朝廷腾不出手吗?连他都会把握时机,卢尚书凭什么觉得我朝内乱时匈奴就只会看着?凭他们收了粮食?”
颜慎怒斥道:“殿下为我们争取到百越的粮食,不是为了让你拿去资敌的!”
这是他们和匈奴比起来唯一的优势——他们能耗,匈奴却不行。
如果连这个优势都丢了,他们必败无疑。
“右相大人是要赌那五层的胜算吗?可别忘了,即使我朝能赢,也绝非一日之功,成王之祸近在眼前,右相大人要如何解决?”
他也生了真火,不甘示弱地骂道:“况且,右相何故一口一个‘殿下’?沈庶人被逐出宗室是先帝亲自下的旨,右相是对先帝不满吗?”
“卢尚书。”沈永和打断他。
他知道卢涵林此刻未必存着政斗的心思,但这个罪名太过严重,真要坐实他就少了一个右相了。
沈永和现在心情也烦得很,他是一个还算有志气、还算负责的皇帝,群臣有多大的压力,他只会比他们更多。
沈永和揉了揉眉心,“左相,你怎么看?”
他最近是不再重用萧予辞了,可他也不得不承认,满朝文武之中,才能胜过萧予辞的几乎没有。
萧予辞俯身拱手:“臣无能,臣不知。”
“真不知?”
“要解此危倒也简单,为今之计,陛下需要一个文官,一个武将。”
沈永和皱了皱眉:“尔等不是文官吗?燕将军不是武将吗?”
萧予辞摇头:“陛下需要的文官要能整合当朝弊病,使百姓归心不生乱;要能持身清正、明察秋毫,为天下文臣典范;要能应对各式各样的天灾,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民生……换而言之,陛下需要的是秦之李斯、汉之孔明,唐之房玄龄,明之于少保……是这等千古难出的人物,臣才疏德薄,难担此任。”
沈永和再度皱了皱眉:“那武将呢?”
“白起、韩信、霍去病、李靖……明敕星驰封宝剑,辞君一夜取楼兰,陛下要的武将,要能在须臾间结束战事,用最快的速度打断匈奴的脊梁,打碎他们所有的奢望,叫他们只能仰望大齐的荣威,不敢踏入我朝国土一步。”
卢涵林冷笑一声:“左相也说此等人物千古难出,这也算简单?”
萧予辞问:“大齐没有这种人物吗?”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武将之中,无人能出燕将军左右。连他都不行,还有谁可以?”
这样的人,不是短时间内在朝野搜罗可以搜罗到的。
此为天授,能有一个都是上苍垂怜。
卢涵林老泪纵横,对着沈永和再度下拜:“天不佑我大齐,还请陛下早做打算。”
萧予辞从容跪地,“有一人,论文治胜于在下,论武功胜于燕将军。”
上苍早就垂怜过人类了,他在人间,这就是证据。
萧予辞道:“陛下何不去信,问一问殿下呢?”
满室寂然。
在卢涵林以“不该称殿下”为由斥责过颜慎之后,萧予辞还用这个称呼,足够表明态度。
半晌,沈永和将他们打发走:“你们先下去吧。”
萧予辞没有多言,从容俯身一礼便起身离开。
颜慎欲言又止,最终还是拱了拱手,一言不发地离开。
其他人倒是想说话,可看天子的神色又实在不敢在这时候触他的霉头,便也叹了口气,相继告退。
唯有卢涵林留了下来。
“请陛下以言语有失治臣之罪,但这话,请恕臣不得不说。”
他俯首行了一个大礼,抬起头时目光坚定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