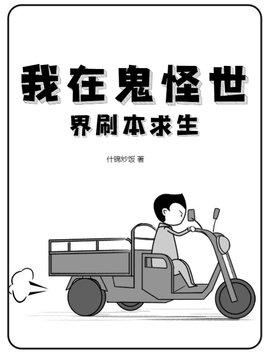书蛋文学>京雪未眠 > 第39章 暴雪夜双更 昨晚一夜没睡(第4页)
第39章 暴雪夜双更 昨晚一夜没睡(第4页)
她知晓他时间宝贵,同她在一起之前,绝不会为了一顿晚餐,在路上耗费大半。
贺问洲从容把着方向盘,嗓音带着让人沉溺的纵容。
“今晚的主线任务是陪我们家小瑾。”他温声,“我所有的时间都是你的。”
下班高峰期的京北被堵得水泄不通,十多公里的路程,开了将近五十分钟。季节菜单做了更新,舒怀瑾点了些没尝过的菜,丹麦甜味洋葱丸子丶蓝鳍金枪鱼配青苹果丶龙虾仔烟熏南瓜南瓜子丶荔枝鸡头米树莓等,搭配的主食她没吃,全推给了贺问洲。
“舒怀瑾,这麽挑食,你到底是怎麽长这麽大的?”
被点名的人理直气壮地挺起胸脯,故意曲解他的意思,“天生丽质呗。”
她穿着件V领长裙,胸前的布料严实地遮住了大片春光,日常看并不觉得有多暴露。
贺问洲眉心压下,轻咳两声,低声斥道:“别在外面勾我。”
舒怀瑾直勾勾地盯着他冷峻严肃的面孔,像是发现了什麽有趣的事,“那被勾到了没?”
贺问洲正在优雅地切着她点的惠灵顿牛排,喉结咽动,保持了沉默。
没有等到他的答案,舒怀瑾暗暗记在心里,一上车便缠着他追问。无奈之下,贺问洲一把握住她的腰,将她往自己身上摁,声线哑得可怕,“勾到了。”
她顺着环住他,在象征着性张力的喉结上留下湿漉漉的口红印,笑容明媚,问出口的话却又如塞壬女妖般挠得人心痒难耐。
“是硬了的那种,还是只有心神晃荡,身体毫无反应?”
贺问洲眉心突突地跳,故作凶戾地掐了下她的腰,“舒怀瑾,能不能有点女孩子的样?”
舒怀瑾一本正经地纠正,“女孩子没有固定的标准哦,贺叔叔。”
“有人温婉害羞,也有人热情奔放,遵从自己的欲望又不是什麽难以啓齿的事,你好古板啊,该不会还停留在清朝思想吧?”
她说到这里,作乱的指尖攻其不备。
贺问洲及时制止,将她细白的手腕扣住,拿她一点办法都没有,妥协沉声:“嗯。”
真从他嘴里听到这个词,舒怀瑾耳朵莫名烧红了,馀光忍不住往底下瞥。
“别看了,已经平息了。”贺问洲气息沉着。
他在她面前总是很狼狈。像被她玩弄得团团转的一只狼犬。
被她掌控欲望,也被她看穿欲望。
她面红耳赤,却还是咬着唇关心,“什麽时候平息的?是刚刚从地库里取车的时候,还是我跟你说想养一条窄头双髻鲨的时候?”
见贺问洲没有回应,她只好将时间线往前推,一步步缩小范围。
“服务员上甜品的时候?”
她心一下子坠落,兀自喃喃:“总不会是加焗蟹肉的时候吧?这才几分钟啊,贺问洲你该不会不行吧……”
没有哪个男人能忍受被人质疑能力。
贺问洲忍无可忍,吻上她的唇。
他吻得太涩情,暧昧的水声在静谧的车内空间分外扎耳,舒怀瑾眼眸潮红,身体也起了一系列的奇怪反应。
这个吻转瞬即至,他似是嫌吻得不够尽兴,一寸寸上欺,直到她退无可退。
“感受到了麽?”
她还未反应过来,脸颊已晕染出一片绯色。
他拂过她的发丝,眸中窜出的烈焰仿佛要将她烧灼殆尽。
舒怀瑾心跳一颤,耳垂被男人以温热的唇舌含住,如同照拂一块绵软可口的云。
她抿着唇,声如蚊呐,“你干嘛……”
贺问洲嗓音沾着浓到化不开的哑意,即便用的是温柔诱哄的语气,依旧难掩骨子里溢出来的强势,“不是觉得我不行?宝宝,这就让你看清楚,到底能保持多久。”
舒怀瑾被他性感磁沉的那句‘宝宝’哄得迷迷糊糊,指尖轻颤着。
“还要多久啊……”
贺问洲忍住想要将她欺负到哭的邪念,挺拔的鼻梁贴近她,“你说呢?”
“我不知道……”舒怀瑾可怜巴巴地说。
她感觉自己变得好陌生,既为他剧烈的反应感到兴奋,又本能地溢出一丝害怕。总觉得清心寡欲的人一旦撕开自我束缚的缰绳,将会变成她无法掌控的野兽。
“你知道。”贺问洲薄唇弧度更深,柔声告诉她真相。
“昨晚它一夜没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