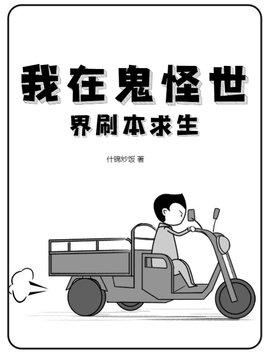书蛋文学>京雪未眠 > 第39章 暴雪夜双更 昨晚一夜没睡(第3页)
第39章 暴雪夜双更 昨晚一夜没睡(第3页)
从前是站不住吃醋的阵脚,才不能多说,更无法承认,如今他名正言顺,有了在意的理由和资本,凭什麽还要容忍其他人卑劣的靠近。
他的确没那麽大度,也并非稳如泰山。
舒怀瑾理清逻辑,试图解读他的言外之意,“你就不能直接承认吃醋了吗?”
她忽而凑近,鼻尖擦过他的面颊,“贺问洲,我发现,你的妒忌心特别强。”
少女清甜的吐息拂过他的唇,有如在同他深吻,贺问洲沉沉注视着她,喉结难耐地滚动一瞬,牵动着他的思绪。
“是。”贺问洲掐住她的下巴,“我吃醋了。”
“现在你知道答案了,也抓住了我的软肋,还要再继续气我?”
“我跟他说了想退出学生会的事,以後应该不会再有联系了。”她们之间的距离不过咫尺,舒怀瑾稍稍往前探,唇峰同他的下唇相擦,过电的触碰激起耳後酥麻的颤栗,她忽然不敢再亲了,望进他的眸子里,“所以你的醋,大概只能吃到今天了。”
贺问洲另一只手掌下移,微扶住她的後腰,有一下没一下地含吻着她的唇。
逐渐粗沉的呼吸落在她颈侧,他冷静地克制着撬开她唇关的欲望,“怎麽忽然想退会?”
“就是觉得没意思。”
舒怀瑾说的是实话,“感觉学生会就像一个小型社会,从主席丶部长丶副部长,到每个部门培养的心腹干事,几乎所有人都野心勃勃,想踩着别人往上爬。可是站在山顶又能怎样?我不喜欢这种利益至上丶人情世故交织的感觉。”
贺问洲:“这个世界的规则本就如此。”
“我想要更纯粹一点的氛围。”舒怀瑾见惯了人情冷暖,也知道自己不该占着好处说这话,但她还处在大学阶段,并不想这麽快被荼毒。
前些日子经历了造谣事件,虽说最後在贺问洲的帮助下,狠狠地打了梁邵的脸,现在连他的嚣张跋扈的尾巴都看不到,爽是真的爽,但仔细想来时,还是会为此感到悲哀。
如果她只是一个平凡的女孩,上了朋友的车,面对无端的恶意,又该如何自救?
“没有绝对的纯粹。”贺问洲耐心十足地引导,“利益纠缠,才能铸就稳定的关系。否则,很容易随着时间推移丶地位差距産生变化。”
舒怀瑾:“就算真的没有,我心里也会下意识想逃避,让它来得更晚一些。毕竟网上都说,少年心气是不可再生之物,非常宝贵。”
贺问洲用指背轻刮了下她的鼻梁,“少看点网上的毒鸡汤,每个人的情况不同,不能强行套公式。”
她低着头欲躲,唇瓣反而被他衔住。
舒怀瑾的心跳扑通,像是海上被风浪掀翻的船只,飘飘荡荡,抓不到锚点。
对上贺问洲深沉温和的视线,她忽然有些不满。
怎麽会有人在接吻的时候,还能心平气和地交心。
不公平。
馀光注意到周遭熟悉的景象,恍若一剂效用缓滞的清醒针,让她後知後觉意识到,他们正冒着随时可能被人偷拍的风向,旁若无人地在夕阳西下的傍晚接吻。
她攥着手指,忽然一动也不敢动,“我知道,我就是想明白了,我没有做生意的天赋,单纯读书我又没有那个一心钻研的毅力,更没有高于常人的精力在官场里如鱼得水,从小到大,唯一能够做好的,就是拉小提琴了。与其东玩西玩,不如专心一件事,说不定还能做出点成就。”
先前吻得太激烈,舒怀瑾的发丝被他揉得凌乱不堪。
贺问洲以指代梳,抚顺她的长发。
“成功是极少数人才能实现的幸存者偏差,不是只靠努力就能获得回报。你还小,没必要对自己太严苛,要是实现不了,过体验式的人生也不错。”
舒怀瑾破涕为笑,嘟囔:“你怎麽跟我哥的想法一样啊。他总说,做不出成就没关系,反正家里是永远的避风港,反正养个奢侈的妹妹对他来说并不难。”
贺问洲:“什麽时候轮得到花他的钱。”
“先花我的,不够你再去啃他。”
虽然是非常动听的情话,舒怀瑾不乐意了,“谁说要你养了。”
“不是养。”贺问洲说,“是来还债的。”
“上辈子欠的?”她追问。
“几辈子吧。”贺问洲淡然的声音十分清晰,“得认真还。”
同她说完这些,他转而正色,“怀瑾,刚才的话不是为了打压你自身的价值,只是想让你知道,从今往後,你所拥有的底气多了一份。至于你想义无反顾地往前走,还是简单快乐地度过一生,我都支持,也相信你可以完成既定的目标。”
只要她快乐,只要她能够为她的观念自圆其说,不会为没有选择另一条路而懊悔,一切的一切都不是问题。
贺问洲的话语有所保留。事实上,他的支持并非一纸空谈的承诺,而是计之深远的砸资源丶人脉丶金钱铺路。艺术价值的高低,掺杂太多主观定义和社会审美影响,而这些有极大部分可以靠资本塑造。
舒怀瑾听完,心头浮出些难以厘清的感动,不管是不是画饼,反正她很满意他的回答。
“我饿了,晚上吃什麽呀。”她勾了下他的脖子,撒娇的话信手拈来,“每到周三身体和灵魂都被掏空了,感觉饿得能吃下一头牛。”
她语气绵软,黏糊糊的,可爱得要命。
或许是怕再度失控,贺问洲身形回正,“具体要看你想吃什麽,西餐还是中餐,都可以。”
“东城区有家米其林一星的店味道还不错,贺大佬不怕堵车的话,我们去那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