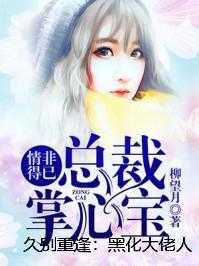书蛋文学>重回高考当状元 > 农家院(第1页)
农家院(第1页)
吃了野果,四人精力略回,继续沿着废路走。
远方隐隐有灯光,那是进入桐山市主城区的方向。
再坚持十几公里,他们就能回到那个他们熟悉的世界——教室、黑板、广播站、饭卡、试卷、喇叭……那个安静而重复的世界。
可他们都知道,他们再回去之后,已经不是同一个自己。
乔伊低声说:
“我们每个人,身上都背着‘不可言说的系统数据’。这场逃脱,不只是现实,更是系统给我们的一次测试。”
陈树点头:“我们通过了。”
胡静看向前方:“但系统会停吗?”
马星遥:“不。它会等我们——去启动它。”
四人朝着城市的灯光,慢慢走去。
他们身后,是风吹草动,是未被监测的夜,是系统之外的一段自由轨迹。
月色退去,天边泛起鱼肚白。
四人顺着荒道又走了二十多分钟,终于在一处低洼地段,看到了远处有些零星的人家——红砖、泥瓦、青灰石墙,有的屋顶塌了,有的院墙破了,但毕竟是“人”的痕迹。
风小了,狗叫声远远传来。
他们沿着一条田边土路走近,来到一座斑驳的院子前。
门是木头的,歪斜地挂着,门缝处贴着一张过年时红纸窗花,已风干褪色。
乔伊轻轻敲了敲门:“有人在吗?”
半分钟后,里面传来缓慢的脚步声,“吱呀”一声,门开了。
是个满头白的老奶奶,身材瘦小,穿着旧棉袄,系着一条花布围裙,脸上皱纹像烟雨旧地图,一双手还端着一个小煤炉灰盆。
她微微眯眼看着他们,眼神略带戒备,但并不敌意:
“你们……谁呀?”
乔伊上前一步,鞠了个躬:“奶奶,我们几个是桐山市的学生,迷了路,这会儿走不动了,想讨点水喝。”
老奶奶看了看他们一身尘土,胡静的脸还有一点红肿,马星遥鞋底破了个洞,陈树嘴角干裂得白。
她“啧”了一声:
“哎哟哟,这是走了多少路……快进来吧,家里水是井水,凉的啊。”
他们进了院子,现这处宅子虽破,却打扫得干干净净。
两扇砖瓦屋之间挂着几条晾晒的布条,水缸盖子上压着一块老木板,菜地里还有半开着的白菜和蒜苗。
最惊喜的,是屋檐下居然挂着一排干南瓜片和红薯干。
老奶奶招呼他们坐下,自己打了一瓢井水,一人倒了一碗:“别嫌凉啊,咱这地方就是没条件。”
胡静接过水,热泪差点涌上来。
她不是矫情,只是过去的焦虑、疲惫,在这一碗清水的“温柔接纳”中,被一股子乡土善意瞬间击溃。
陈树喝完水,望着院子说:“奶奶,家里就你一个人住?”
老奶奶叹了口气,慢慢说:
“我儿子在青岛做工,闺女出嫁到皖南了。这屋子啊,也就我一个人守着。人老了,也不想去城市了。”
她顿了顿,补了一句:
“不过啊,咱这地方,种点菜、劈点柴、喝点水,也就够活了。”
乔伊环顾四周,说:“奶奶,咱们做点早饭吧。你歇着。”
老奶奶笑了:“哪有客人下厨的理儿?”
胡静笑:“这会儿,咱不是客人,是徒步逃命到家门口的‘困小孩’。”
四人张罗起来。
马星遥提着一把小斧头,跟着老奶奶去后院劈柴;
陈树蹲在灶台边生火,把旧报纸团得像小时候学的;
乔伊洗菜、淘米,水缸一勺一勺地提;
已完结热门小说推荐
- 阮流苏周容儿流年深深深几许:结局+番外阮流苏周容儿
- 我看着她,忽然又想到第一次见到她时,她清纯羞怯的模样。不知为何心底有些唏嘘。嗯,听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