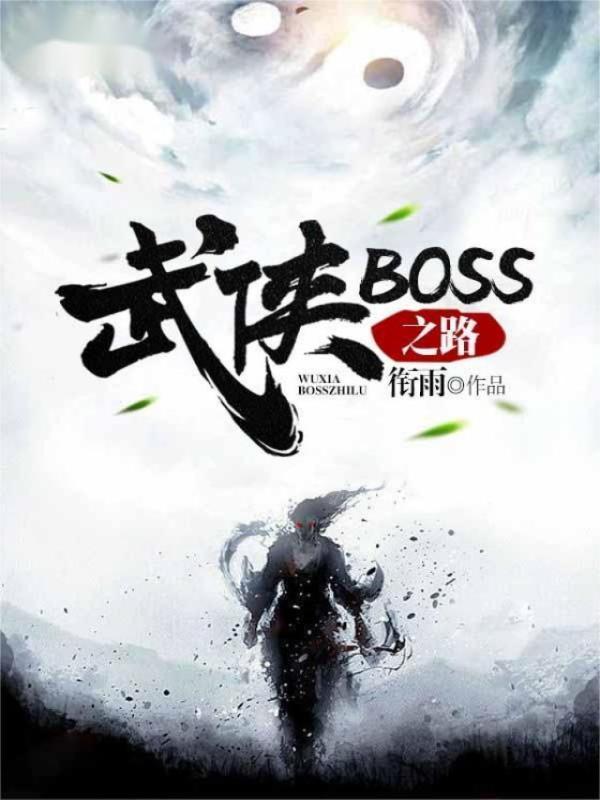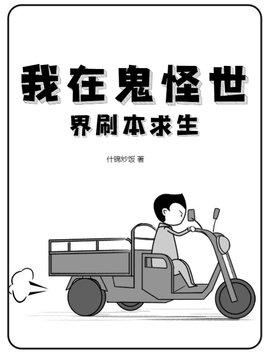书蛋文学>重回高考当状元 > 6剧本之外在青春的坐标系里没有谁是局外人(第4页)
6剧本之外在青春的坐标系里没有谁是局外人(第4页)
青春期的敌意从来不需要理由,它可能藏在作业本的边角,也可能只是因为一杯奶茶递错了人。
但她很清楚——她必须留下来。
那天晚上,乔伊坐在床上,物理作业摊在腿上,窗外的风吹动蚊帐,出“哗啦啦”的轻响。
她看着窗户上映出的自己,觉得自己像一张还没完全显影的照片。
那个年代没有微信,没有社交软件,很多情绪都藏在小动作里——
比如换掉的值日表,消失的橡皮擦,被压低语气的问候。
她忽然想起妈妈说过的一句话:
“重点中学其实就是一个浓缩的小社会。”
她以前不信,现在信了。
【马星遥·她们像三种不同的函数】
傍晚的阳光斜斜洒进教室,尘粒在空气中慢慢打着转,落在每个人的肩膀上,也落在马星遥的眼睛里。
他撑着下巴看向前排——乔伊、张芳、王昭,刚好三个人肩并肩,像试卷上的三个函数图形,各有各的轨迹。
乔伊安静地翻着题本,动作不快,但特别专注;张芳在演算纸上写写擦擦,一点没浪费时间;王昭侧着身跟同桌说笑,偶尔转头,也总能引起几道视线偷偷追随。
三个人,像三种完全不同的节奏。
马星遥一边转着笔,一边默默想着:
要是能建个公式,把她们的“变量”全带进去,是不是就能解开这个教室的所有谜题?
但他也知道——乔伊,根本没办法建模。
她不像张芳那样逻辑清晰,也不像王昭那样自带光圈。她更像一道你看了很久、觉得会很难的题,但真正动笔后,却又现它静静地躺在那里,从不主动告诉你答案。
他记得她有个小动作。
每次看题时,她都会用食指在纸上无意识地画圈,像在确认一个坐标点。圈圈重叠,最后成了一团模糊的墨迹。可她不急,也不擦,就让它那样在那里,像一种默许。
有一次,她在物理课上指出老师的一个板书错误。
没高声强调,也没特意解释——只是举了下手,说:“老师,这个单位应该是焦耳,不是牛顿。”
她说得很平静,但马星遥那一刻看了她一眼——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光从窗外洒在她侧脸,她的影子落在墙上,那种“安静地光”的感觉,他这辈子第一次见。
从那以后,他开始留意她。
看她用红色的笔改作业,看她在打铃那一刻迅收拾桌面,也看她在别人聊天的时候,总是轻轻低下头,继续写自己的题。
她不说什么,也不想引人注意。但偏偏就是这种人,让人无法忽视。
有一节数学课,他忍不住回头看她。
刚好她也抬头,视线对上了。
那一秒,他居然有点慌。
她的眼睛不像王昭那种带笑意的明亮,也不像张芳那种波澜不惊的冷静,而是那种——你看进去了,却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他正出神,老师点名叫他回答一道三角函数题。
“马星遥,你来。”
他下意识站起来:“π。”
老师点点头。
坐下时,他低头看了眼自己的草稿纸,才现整页已经被自己画满了波线——
一波接一波,像电流,又像情绪。
他有点懊恼地揉掉那张纸,却忍不住多看了眼前排那根微微翘起的马尾辫。
【张芳·她是那种不容易被记住情绪的人】
张芳一直是班里最安静的那种人。
她的笔记干净到不像高中生写的,字像是量好格子印出来的。
每天第一个进教室,最后一个离开。连喝水、上厕所的节奏都能对得上钟表。
她不说废话,不加别人qq,不参与讨论。不是高冷——只是没必要。
马星遥和她是因为竞赛才熟起来的。
那次放学后下雨,全班人都走得差不多了,他还在黑板前抄题。
她走到他桌前,递给他一张草稿纸:“这两道题你的思路有点松动,尤其这一步推导,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