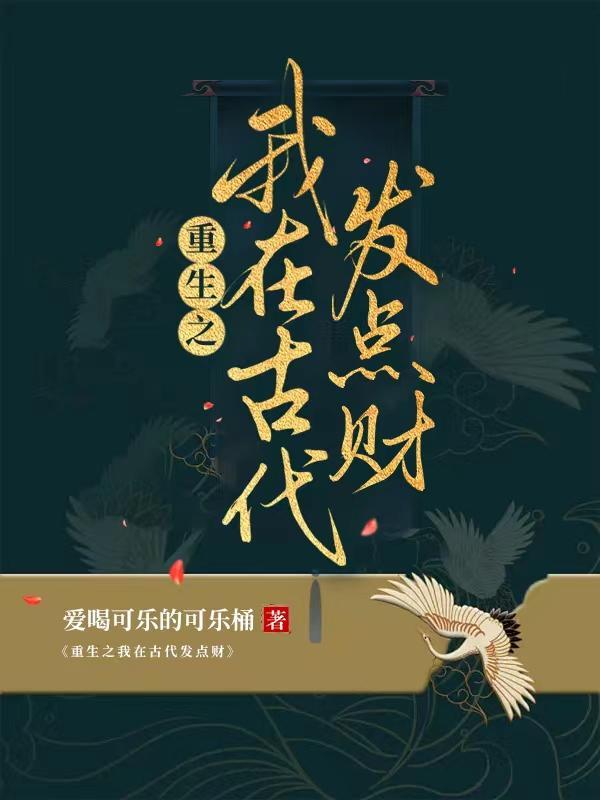书蛋文学>[三国]据野史记载…… > 3君子六艺无茶艺(第3页)
3君子六艺无茶艺(第3页)
但说归说,闹归闹,袁珩好歹要拜荀氏子为师,按大汉风气,这与拜为义父没什么区别,而对士族门阀而言,拜师是比之更亲近、更紧密的联系。
懂不懂门生故吏的含金量啊(那种语气)。
袁基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荀爽虽不知道袁氏兄弟矛盾内情,却知道袁基比袁绍更通人性的热知识,再加上袁基暗示会帮他挡一回朝中征辟,也就应下帮忙作证以及引荐许劭。
而后荀爽提起一件袁基一无所知的往事。
“子将曾与我二兄‘无意’提及,三年前濮阳令携爱女返乡时恰逢月旦评,便将珩女公子的文章送了过去。”荀爽声音压得很轻,“而后子将与女公子清谈近半个时辰,给出了评语,却被濮阳令按下不提。”
袁基闻言,表情一顿。
月旦评之所以被时人推崇,很大一个原因就在于许劭、许靖从不会谄媚权贵;但袁绍强行压下袁珩的评语,许劭竟也不曾计较,这就很值得深思了。
……其实也无需深思。
端看袁绍状似不顾大家死活的筹算,就能猜出一二来。
袁基没有问荀爽知不知道评语、评语又是什么,若无意外,明日荀绲自会坦诚相告。
他只是微微笑了笑,似浑不在意,温声:“竟如此么?想来我这为人父者,还要对儿女多加了解才是。”
夜风微凉,明月朦胧,树影斑驳间,袁基的笑意并不明朗。
荀爽笑而不语。
*
次日用过朝食,袁珩便见到了自己的先生,荀攸荀公达。
荀攸刚及弱冠,模样斯文俊秀,与袁基、袁绍相比固然略显寻常,但一身诗书风雅气质浓郁,比袁基还要年轻七八岁的人呢,往那儿一站就是教导主任。
可一开口,那股青年人特有的活力便露出些许:“我读过珩女公子的文章。女公子麟子凤雏,来日可期。”
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是客套话,但而立之年喜提贵女的袁基很爱听:“阿珩还小呢。”
大家都以为是自谦。
只有袁珩没忍住捻了捻指尖——听起来伯父这话后头,该接的是“长大了更了不得”。
荀爽在旁边倒是看得分明,不由打趣:“公业这话若是随着珩女公子的文章一并传出去,怕是天下所有人都要觉得你不知足啦。”
袁基心想,我已经很克制了,没临时变卦叫她拜你荀慈明为师,都得算我看重礼仪。
袁珩直觉哪里不对,有些敏感地看了眼袁基。
袁基拍了拍她的脑壳,笑吟吟道:“该行拜师礼了。”
袁珩只能压下疑虑。
正衣盥手,先向孔圣行九回叩首礼,再向荀攸行三叩首礼;拜师帖递去,六礼束脩献上;茶烟袅然氤氲,也晕不开荀氏公子脸上真切的笑意。
荀攸并未按时下规矩训诫,只温和看着她:“戒骄戒躁,修文修身,方不负己。”
哪里是训诫?最多称得上提点——可见荀攸当真满意袁珩的资质。
拜师礼成。
忽而一道清润嗓音自座中传来,袁珩循声看去,入目便是一张清光玉面,温润俊雅。
他开口便是很符合少年模样的些许促狭:“公达,你给珩女公子备了什么见面礼啊?”
所以说啊,有时候命运就是这般奇妙,轰轰烈烈的开场大多都兰因絮果,但寻常得几近乏味的初遇却可能是千古佳话的缘起。
袁珩多年后回忆起今日,也深觉这一幕毫无宿命感——主角是她与荀攸,他不过是满座荀氏子弟之一,若非他突发奇想似的神来一笔,她或许还要过许久才能见到他。
可除此之外呢,却又有丝丝缕缕无形的细线缠绕着交错勾勒,于是只一眼,哪怕史书上对他少时记载寥寥,而光和三年秋的少年郎君尚不似日后居中持重的老成,唯能窥见一二与生俱来的如冰之清,袁珩也有一万分把握笃定他的身份。
是他。
荀彧,荀文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