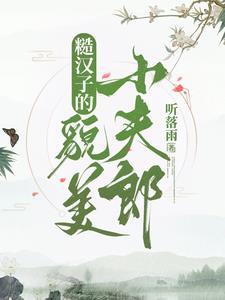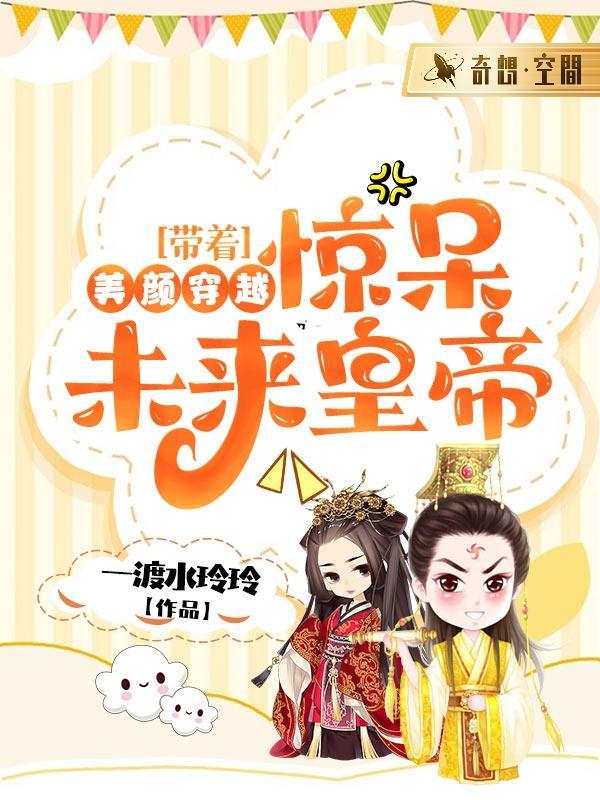书蛋文学>别青山 > 160170(第8页)
160170(第8页)
床被下,范春霖蜷缩着身子,骨头的轮廓都清晰可见,瘦得令人心惊。
程荀看着他数日内飞速憔悴下来的模样,抿抿唇,问道:“要将满墙血书用柜子盖住,不是易事。你当初,为什么不直接将整座楼都烧了?”
范春霖被程荀问得一愣,怔怔地望着床帐上的纹理,半晌都说不出话。
于他而言,十四岁的一切,都像个遥远而缥缈的梦。如今回忆起来,好似眼前蒙了层纱,摸不透、看不清,甚至时常令他怀疑,一切或许只是他酒后的一场臆梦罢了。
翻入藏书阁的那天,他依稀记得是个傍晚。
黑暗的藏书阁内弥散着一股腐朽陈旧的气息,排排列列的书架上不是梵语写就的晦涩佛经,就是庙里多年来的种种记录,没一会儿,范春霖就失了兴趣。
直到他走到藏书阁顶层。
如血的残阳洒落一地,他循着夕照一脚踏入顶层,此生就此转向另一条岔路。几面墙上刻满了凌乱潦草的文字,他一眼望过去,却看到了令人心惊的几个字眼。
“沈家军”“范脩”“细作”“战败”……他将那墙上的文字翻来覆去读了数遍,直到最后腿一软,直直跌坐在地。
脚边有一块松动的木板,他木着脑子将其推开,发现了其中藏着一具蜷缩的白骨。
那一刻,他的整个世界天崩地裂。
若说方才心中的怀疑还有三分,直到看见那具白骨的瞬间,他几乎可以断定,几年前瓦剌绕过七卫突袭漠南、沈家军出人意料的节节败退、沈仲堂命丧漠南,桩桩件件,恐怕都与范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那么,他能怎么办?
一走了之,当做一切都没有发生,继续做他家世显赫、声名远扬的西北总兵之子?
还是大义灭亲,带着证据逃亡京城,敲响那一座登闻鼓?
从月升待到天明,范春霖与那具白骨对坐一夜,最终下定决心:至少,他该亲自求证一二。
他既不敢将这一切坦然露在原处,也不敢一把火将一切毁之一炬,只能笨拙地、费力地从别处搬来柜子,将那满墙的绝笔血泪牢牢盖住。
他想,他不过暂且将一切盖住罢了,待他查明真相,他就,他就……
在金佛寺待了整整三天,他带着一身尘泥、两手红痕,疯了似的跑回了家。
到家后,范脩、段氏只嘴上责备他两句,欢天喜地为他接风洗尘。
之后的一段时日,他旁敲侧击打探过,偷摸进父亲书房搜寻过,都未能寻找到范家暗害沈家的证据。
悬在半空的心终于落了下来,范春霖将金佛寺那有如置身地狱的几天当做南柯一梦,将满墙绝笔看作罗季平发了疯的污蔑。
他想,他要找机会将一切都告诉父亲,可不知为何,他却迟迟开不了口。
直到一天夜里,他终于下定决心要向范脩坦白,却在书房外无意中听见了范脩与属下的低语。
屋内,那位向来偏宠他、以他为傲的父亲,用某种他陌生的语气,怒斥哈达部落胃口大、伊仁台不守信,明明已经约定好将肃州下的两个村镇给哈达打牙祭,却还妄图将手伸到肃州城。
范春霖听得云里雾里,又听那属下小心提醒瓦剌人多狡诈、伊仁台更是老奸巨猾。
范脩却无奈道,当初因为沈家的事,把柄还落在伊仁台手中,如今也只能暂且妥协。况且,区区两个村镇,给了就给了吧。若没有哈达时不时骚扰一二,新帝上位,不必等沈家倒台,第一个倒的,就是他范家。
属下在旁附和,就算现下应付伊仁台麻烦些,至少借瓦剌之手将沈家铲除了。若非将军先下手,谁知沈仲堂已经查到了哪一步?
范春霖浑身有如雷劈,紧紧捂住自己的嘴,悄悄逃回了自己屋子。
当夜,他烧起高热,满口胡话。段氏衣不解带在旁照料一夜,听清他口中的话后,骇得满脸煞白、跌坐在地。
待到天明,范春霖终于从高热中醒来,却见屋中空无一人,只有段氏跪坐在他床前。
他头昏脑涨,茫然发问:母亲,您这是做什么?
段氏抓住他的手,将他攥得生疼,布满血丝的眼里尽是恐惧与哀求。
然后,她从袖中抽出一把匕首,拉着他绵软无力的手,抵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她说,春霖,我的儿,你是范家子,莫要做出愧对范家之事。
她说,春霖,若此事捅出去,范家毁了,你这辈子也毁了。
她说,春霖,若你说出去,娘亲横竖都是一个死,不如现在就死在我儿手里吧,总好过被关进天牢,平白让京城的亲戚看笑话。
范春霖身子僵住,一颗心如坠冰窖。
他想,他的母亲,他那事事为他着想、他那贤名远播的母亲,果然是世上最了解他的人。
她明白他的两难、他的痛苦、他的软肋,然后利落干脆地将这一切当做筹码,赌他会妥协、会低头、会闭嘴。
母亲赢了。
而那个名冠汉中、少有才名的范春霖,彻底死在他十四岁那年。
往事纷至沓来,回忆如一本旧书,残破的书页在他眼前随风而动。他看得痴了,迷迷糊糊中,才听到程荀问道:“五年前,为何要给辩空传信?”
范春霖这才如梦初醒。
他看向程荀,开裂渗血的嘴唇嚅嗫道:“五年前……善儿,我的善儿……”
话音停顿许久,程荀才听到他低沉沙哑的声音。
“范家人,此生都是背负罪孽的。”他挣扎着坐起身,瘦得枯槁的手在空中比划着什么,“我的善儿,应该堂堂正正地活着。”
范春霖的话前言不搭后语,程荀轻易听懂了,一时默然。
他屈服了,浑浑噩噩活了几年,因为新生的血脉,终于鼓起微弱的勇气,向同样心怀执念的辩空送去了蛛丝马迹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