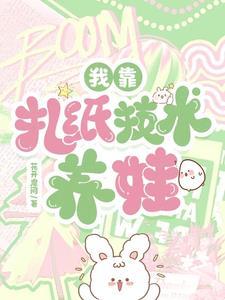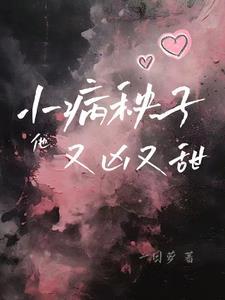书蛋文学>别青山 > 120130(第16页)
120130(第16页)
西路大军内部鱼龙混杂,各部族从前在草原上便有不少夙怨,相处起来更是摩擦不断。
更何况,谁又真的愿意为阿拉塔嘴上一个“荡平大齐”的壮志去卖命呢?即便阿拉塔将来得偿所愿,他身边的心腹那么多,他们这群临时被拉来的“外人”又能得到多少好处?能喝口汤就不错了!
战事之初,瓦剌数万大军攻城略地、有如神助,齐军的溃败快到不符常理。不过一月的时间,阿拉塔便将兵线推至肃州外。
可自从扁都隘口一役后,双方却进入了几乎停滞的状态。据晏决明的分析,或许一方面是大齐朝廷增员兵马的“及时”反应;另一方面则是阿拉塔起初将兵线铺得太开,后续却难以为继。
看到这,程荀不禁皱眉。
她总觉得,事情恐怕不止表面这般。
她接着往下看。
本就摇摇欲坠的信任与共识,在昆仑山下日复一日的等待中逐渐消逝。
时值寒冬,兵士们被迫驻守荒凉苦寒的大漠之上,等待迟迟未到的号令。
东、北两路大军有阿拉塔及其心腹大将坐镇,暂且掀不起什么风浪。
可对于西路大军而言,粮草不断消耗、内部摩擦频频,就连此前唯一的念想——在入侵途中多屠戮几座城池、多捞些好处都做不到了。原因无他,昆仑一带哪里找得到什么重镇、大镇呢?
因利而来,势必因利而往。
得知西路大军人心动荡、管束松散,晏决明便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
之后的谋划必想象中还顺利。晏决明先是一连截断了西路大军的数次传信,阻绝了上层将领与阿拉塔的联系;
而后,再往军营中放出些或真或假、影影绰绰的消息,或是瓦剌前线已然溃散、或是阿拉塔重伤休养,不断弹压底层将士的情绪。
而真正的导火索,是一场不起眼的斗殴。
几个来自不同部落的将士,私下相约“切磋”,在斗殴中“失手”杀死了其中两人。
一位来自哈达部落的将领负责处理此事,而他态度敷衍,只随意处罚了剩下几人,妄图息事宁人。
可翌日,几名斗殴者,连同那位实行惩处的主将,都死了。
他们的尸体被人悬挂在各自部落的主将营帐外,浑身□□,死状极其残忍。在瓦剌习俗中,那样的死法是无法在草原安眠、重回母亲河的。
——这无疑是种挑衅。
对于一群困守雪原数月,早已被疲惫、焦躁与绝望折磨至麻木的兵士而言,族人的受辱,是他们终于得以寻到的发泄口。
汗与血在军营中迸溅,愤怒的嘶吼、张狂的咆哮交织成冲锋的号角,他们拿起武器劈向身边或陌生、或熟悉的瓦剌同族。
西路大军哗变了。
骚乱持续了一整日。士兵们杀红了眼,本就各怀异心的上层将领收拾钱财、准备作鸟兽散。
而晏决明的人趁机混入其中,在□□的人群中利落地手刃了妄图逃跑的将领。
直至翌日黎明,哗变才终于平息,换来的是整个军营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就此,除却部分借机溃逃的瓦剌士兵,阿拉塔原本引以为傲、视作一统草原的象征的西路大军,就此溃败。
看到最后,程荀长长地舒了口气。
在信中,晏决明并未对整个过程进行太多渲染与强调。但以区区三百将士攻破近万人的西路大军,哪怕是智取,其中艰难也可想而知。
但凡错算一点时机、错失一分运气,今日结果都不会如此。
悬在半空的心终于落下。程荀倚靠着木窗,闭眼缓了缓神。待眩晕感稍稍消退,程荀将信丢进火盆里烧尽,才拿起放在一旁许久的木盒。
木盒形状细长,程荀轻轻握着,心中已大致有了猜想。
打开木盒,果不其然,其中静静放着一支木簪。木簪素雅简单,只在尽头做出一簇兰花的样式,看上去平平无奇。可拿到手上,木簪却很有分量。
程荀缓缓转动角度,竟在角落微微绽开花瓣的花骨朵里,透过那狭窄的缝隙,看见一个由花蕊组成的、小小的“六”字。
她一时忍俊不禁。
刻了自己的记号,却偏偏藏在这么不起眼的地方,明明笃定她一定会看见,却还要装得姿态云淡风轻。
嗯,这做派特别晏决明。
程荀嘴角微扬,走进里间,就着铜镜将木簪插到发间。照影中,她目光忽地一凝。
取下木簪,她蹙眉打量片刻,试探性地推了下那刻了字的花骨朵。
下一瞬,伴随一道破风声,那木质的簪尖上竟然冒出了一段与簪身相当长度的利刺!
程荀吓了一跳,这才明白,原来这木簪是件防身的机关造术。只要轻轻一按花骨朵,那尖刺便又能收回去。
她眨眨眼,指腹轻轻摩挲着木簪上的兰花。
“也不写张纸告诉我。”
她在心中小声道。
半晌,书房的门终于拉开。闻声,站在廊下低声说话的几人赶忙走上前。
程荀已整理好情绪,平静道:“进来说吧。”
进屋后,程荀开门见山道:“大致情况我已知晓了。你直接告诉我,此番回来,是为何事?”
冯平坐直身子,道:“回主子,将军命我带走神隐骑,随他一同去前线。”
程荀一惊,心骤然缩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