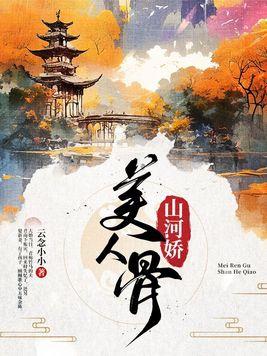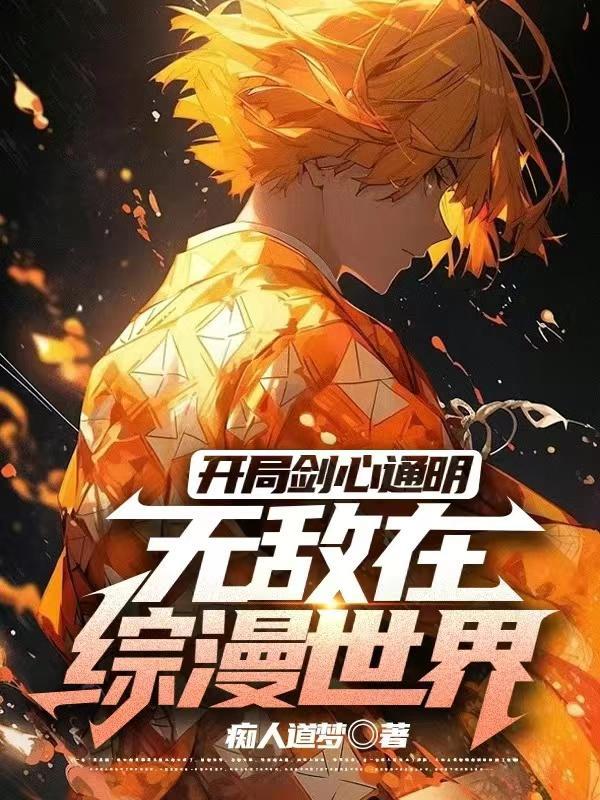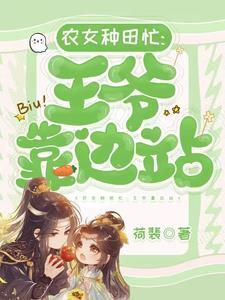书蛋文学>我真的是咸鱼[快穿] > 第29章(第2页)
第29章(第2页)
来的人多,御书房也如一个小朝堂。当他们分成两个立场各执一词的时候,便像一场小朝议。
“荒谬,一朝藩王死得突然,若是将此事轻轻揭过,才是叫国朝颜面扫地。”
“办法总是有的,对外斥责成王悖逆,重赏苏千慕为君分忧。”
“这如何使得?苏千慕分明无忠君爱国之心,她亦曾剑指陛下,怎么能颠倒是非?”
“吴大人忠君爱国,吴大人守律法,不知成王冒犯天威时,大人在何处?”
小朝议泾渭分明分成两个团体,一方寸步不让,一方随之反唇相讥。
沈永和端坐高台,不动声色看着两方唇枪舌战。
这也是先帝教他的帝王之术——当朝臣有矛盾的时候,先不必急着发话,他们说的内容不是最重要的,但他们的立场很重要。
谁与谁站在同一方?谁维护谁?谁平时看上去是清流孤臣,实则每次说话都有人附和?
这些背后代表的关系交错,才是为帝者真正要重视的事情。
他年少时不懂,全是先帝在早朝后专程留他下来,一点一点细致地教他。先帝对沈明烛不是慈父,于他却切实倾注了满腔爱意。
谁都有资格怪先帝过于偏私,以使大齐失了圣明君主,唯独他不可以。
因此沈永和对沈明烛的感情很复杂,好像他一旦开始心疼、欣赏对方,就抹杀了先帝的价值与付出。
沈永和难得在议事时失了神,他再一次想起了已经逝去的先帝。
父皇,您当年是怎么想的呢?您知道皇兄之才如腾蛟起凤,有鸿渐之仪吗?
如果您知道,您又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决心让儿臣继承皇位?
这天下不止歇的灾祸,难道是上苍对你我的惩罚吗?
……可是父皇,儿臣还是好不甘心啊。
沈永和看着底下为苏千慕争取到面红耳赤的臣子,那里面有他引以为左膀右臂的两位丞相,有礼部、户部、兵部三位尚书,还有其余十数人,占了今日来此大臣的半数有余。
他们与苏千慕并无私缘,为苏千慕说话,本质上是在为沈明烛冲锋陷阵。
沈明烛没有下过任何命令,是他们仅凭着几分猜测,于是便可以不在乎曾经苏千慕对他们刀剑相向,转而为她摇旗呐喊起来。
看,多轻易就改换了立场?
不过是沈明烛半年不到积攒起来的班底啊。
“都安静。”既然已经看清楚各自阵营,沈永和也就叫停了争论,他朝左右道:“拟旨,成王沈秉欺君罔上,私收赋税,蔑伦悖理,逆道乱常,不知悔改。为求活命拥兵自重,意图祸乱朝纲,罪无可赦。义士苏千慕仗义执剑,虽有冲动行事之嫌,然拳拳报国心天地可鉴,特赦其无罪……”
他说完,看向朝臣:“诸位爱卿可有异议?”
为苏千慕说话的人得偿所愿,自然没有意见。
站在沈永和这方的人见他已经做了决定,也不会反对,只难免还是有些顾虑:“陛下,这会不会……”
沈永和没有理会,他自顾自继续道:“既都无异议,朕便说第二件事。前线的战报送了过来,就在昨日,东边我朝与回鹘主力开启交战。”
他顿了顿,一字一句道:“惨败。一日之内,回鹘连下吉屏、善谷两城。”
内侍躬着身,将誊抄好的前线文书挨个递给在场的朝臣。
自大齐建朝以来,只有他们打败其他小国开疆扩土的份,这还是第一次国门失守。
朝臣俱皆骇然,失去国土的耻辱与无颜得见先祖的羞愧混杂在一起,主战者更勇,主和者更怯。
——当然要收复失地,否则他们这些食君之禄的臣子,这些受黎明供养的官员,何以谢天下?
——但是再打下去,又输了怎么办?若是早听他们的话,送些粮食金银出去,吉屏、善谷根本不会失!
沈永和仿佛没听到他们的争论与私语,他接着道:“北境幸有燕将军镇守,暂寸土未失,可形势也不容乐观,伤亡可谓惨重。飞虎卫回防,洛阳大军也到了长安,朕打算让江铖率领他们,带着粮草北上支援。”
朝臣们弗然色变,尤以坚定拥护他的那批臣子表示得最为激动:“不可,陛下不可啊,中枢防卫空虚,若是有个什么万一,后果不堪设想!”
“您是天子,万金之躯,如何能置身险境啊?”
沈永和耐心解释:“成王已死,藩王们人心惶惶,不敢有异动,各地又有驻军在出不了大乱的。”
这当然说服不了他们,朝臣们纷纷跪地:“请陛下三思。”
“不必再劝,朕意已决。大齐可以亡,但华夏不能有失。”沈永和语气蓦然染上几分沉重:“大齐若亡于朕手,朕当发覆面,口中塞糠,以告先祖。尔等都是国之柱石,无论后继者谁,只要能收复失地,善待百姓,便不失一代明君,请诸位爱卿无需顾念朕。”
仿若至穷途末路的悲怆一下子遍布整间御书房,反而爆发出令人震撼的决心与生命力来。
如果连身为皇帝的沈永和都做好宁可身死也要拒异族于国门外的决心,他们身为臣子,又怎么能拒绝呢?
九州先是一体,而后才属于齐朝。
于这驰魂宕魄中,萧予辞一丝理智尚存,他敏锐察觉到一丝不对劲之处:“为何是去北境?那东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