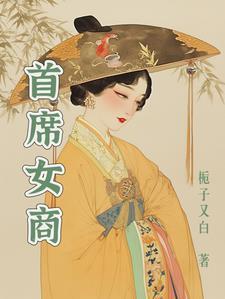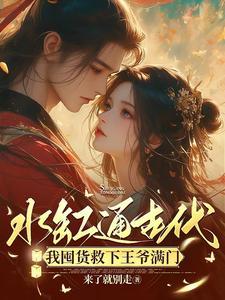书蛋文学>谋杀黄昏 > 第13章 真心换真心(第1页)
第13章 真心换真心(第1页)
春末的风温度不冷不热。
陈寄站在原地,似乎明白了情况,略有嘲讽地反问:“就因为我说没把你放在眼里?小学生也不至于那么幼稚。”
林思弦回望着他。陈寄穿了一件黑色短袖,尺寸偏小,骨骼在布料上顶出轮廓,细看发现手肘和锁骨上有几道微小红痕,之前那场架他也不是完全没受伤。
他特意没穿校服,看起来做好了继续以肢体语言解决的准备,譬如原地不动让林思弦痛殴一顿,来换取那张营业执照。
但林思弦显然没有让他如愿:“幼稚吗?好像是有一点。那你也可以不做,选择权在你。”
十分钟,六百秒,三首歌,四分之一节课,不短不长的时间。
林思弦不知道自己在陈寄眼中什么样,陈寄情绪几乎不外露,也不知道他此刻在想些什么。但林思弦并不在意。他们离得不算近,他没办法从陈寄瞳孔中看见自己的倒影,但他知道他肯定真实存在于陈寄视野里。
没有人计时,同班同学推门而入的谈笑声成了天然闹钟。
第三个进来的是语文课代表,他嗅到了一丝战场的气息,又敏锐道:“两位同学在干嘛?没发生什么吧?”
林思弦又很礼貌地回复他:“之前我跟陈同学有点小误会,刚才偶然聊了点心里话,将心比心,误会已经解除了。”
他从讲台上下来,走到陈寄旁边,略微抬头,送给他一个很灿烂的笑容:“我们以后就是朋友啦。”
林思弦在第二天夜晚接到了姨父的电话。
姨父对他向来都非常客气,每次家庭聚会时都会以不同的形容词来夸赞他,来电时也并没有直入主题,而是先嘘寒问暖了几句,才委婉他跟陈寄在学校是不是关系很好。
“还不错,”林思弦说,“他们家很困难吗?”
“是有些难处,”姨父大概花了一天时间在庞总跟林思弦当中权衡,并且做好了决定,于是对于陈寄家庭的描述多了怜悯与仁慈,“他母亲靠这个店独自抚养一对兄妹,听说还有个老人在医院住着,不久前还因为医疗费产生了点纠纷。”
在林思弦的引导询问下,姨父多讲了一点内容。陈寄他父亲以前是电子厂员工,几年前的一个深夜,送完醉酒的领导,自己独自骑摩托车回家,路上疲劳驾驶出了事故离世。
原来他父亲的死因是这样。林思弦突然回想起陈寄在跨年那夜的酒吧门口,看垃圾一样的眼神。
通话的最后林思弦说:“姨父,营业执照没问题的话,你平时定期派人去他家店里看看吧,关照关照,医院那边也帮忙看看,我学习忙,没事帮我送个果篮。”
姨父答应了,再度夸奖他:“思弦,你人心善,未来肯定会有福报。”
林思弦当然没打算做慈善。所谓的关照不过是提醒。告知陈寄所有的果篮都有标价,而这些价格都需要陈寄来支付。
这个道理他跟陈寄都很明白。
按照常规说法,形成一个习惯需要二十一天。但大约陈寄天赋异禀,或者好学生适应力比较强,林思弦第二次叫他的时候,他没有再对林思弦的要求提出任何质疑。
林思弦让陈寄帮他做了两天的数学和英语作业,并且要错得恰到好处,陈寄没有回答好或者不好,林思弦也没有苛求他的回答,但在第三天早上,林思弦还是在自己桌上看见了完成好的四张卷子。
大多数时候,林思弦让陈寄完成的都是这一类常规的需求。
譬如在排队很长的小卖部替他买一瓶果汁,譬如在课间帮他骑车去三公里以外的电影院买一张电影票。
偶尔也有一些常人无法理解的指令。
那一周林思弦看的是一部文艺电影,末尾画面上出现了很长段的文字,引用了西方一位作家的几句诗歌。林思弦在网上查到了作家的一本诗集,让陈寄去图书馆帮他借这本书。
“学校图书馆没有这本书,”陈寄去完之后告诉他,“管理员说只有区图书馆才有,但是学生办不了那里的借书证。”
林思弦很快就想到了解决方案:“那你去帮我把那几首诗抄下来。”
“林思弦,”陈寄平静地提示他,“你在网上就可以看。”
“我知道呀,”林思弦说,“但我不喜欢在网上阅读。”
三天之后,林思弦得到了他需要的东西。他很熟悉的字体誊抄的几首陌生的诗,写得很工整,连一个错字都没有,只有几笔写得太重,将那几页白纸戳出了几个小洞。
*
娄殊为最近觉得这个世界出了一些问题。
自从之间打架事件以后,他受到了非常严厉的惩处——没收了游戏机和零花钱。
事态严重到他都开始思考人生,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的爱情在哪里,我的零花钱又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