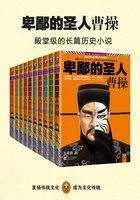书蛋文学>枕流光 > 第24章 二十四 傩面(第2页)
第24章 二十四 傩面(第2页)
“喝的这般豪放,可尝出味儿来了?”谢渠打趣道。
杞瑶一点都不心虚,“这酒品性烈得很,唯有痛饮才不算辱没。”
谢渠没接他的话,而对面杞瑶早停了筷子,大着舌头嘟囔着什麽,显然是酒意上来,开始醉了。
“我当日在太极殿上那番话很是不妥,我以为依你之能,不可能将这案子查下去,”月色落在杯中,覆了浅浅一层白霜,谢渠声音极轻地开了口,杞瑶却没听见。
他从杞瑶手里接过酒坛,给自己又添了一杯,接着说了下去:
“此事是我鲁莽了,合该向你道歉才是。”
杞瑶擡起脑袋,迷糊应了两声,只有最後一句“殿下慎言”被谢渠听了个清楚。
他不经失笑,那笑容映衬着清晖朗月,自然地沾上了几丝落寞的味道。
“是我失言了,嗯,甚麽?”谢渠见杞瑶忽然起身,冲着门外去,当机立断也拿了件披风跟了上去,“瑶儿要去何处?”
杞瑶被门口的冷风一吹,霎时清醒了几分,但仍旧记挂着要出去:“外头有灯会,我……我要去看!”
谢渠当然不会和醉鬼计较,只得替他披了衣服,宠溺道:“小心脚下。”
一墙之隔,飞廉头一回悟出了何为有眼色,他轻手轻脚地替二人将门带上,心中盘算着是否要挑个良辰吉日,去裁正司与庭燎庭大人交个朋友了。
月上柳梢头,花市灯如昼。
君瑶走後,杞梁当然不会带杞瑶出府看这些热闹,故而杞瑶自记事起也没逛过几回灯市,看什麽都觉着新鲜,谢渠更不必说,行军打仗去的都是苦寒之地,而除夕夜里宫中内外挂的彩灯,往往千篇一律,薄如蝉翼的纸上绘有寓意吉祥的彩画,再用丝縧系过挂在廊下,如此便算是宫里的灯会了。
用杞瑶的话说,便是美则美矣,却少了三分烟火气。
夏令时节的灯会自然与元月里的不同,最为明显的一点,便是河道两岸皆人流如注,摩肩接踵,杞瑶不得不贴紧了谢渠,才勉强不至于被人群分开。
谢渠见他意识时而清晰时而混沌,干脆拉过杞瑶的手搭在自己臂弯上,免得他被挤走。
“瞧二位小爷这身打扮,便不是寻常人家,嘿!小的绘面的手艺是为家传,二位不妨来看看?”
人流中,有一人挤上前来,手里还拿着一柄杆子,上头挂满了东西,谢渠纵使再少有经验,也知道这人一串话是自吹自擂,算不得真。
偏生杞瑶晃晃悠悠走了两步,随手在那杆子上取下一只傩面,贴近了谢渠的脸道:
“大哥,戴不戴?”
谢渠透过傩面纤长的两眼,直直盯着杞瑶,一动不动地沉默着。
杞瑶笑自己自讨没趣,多亏有醉酒这一名头替他掩护,倒也不算太过分。
他觉得自己或许当真是醉了,或许是把谢渠那句“眼下我算不得东宫太子”当了真,便趁着酒劲开脱道:
“大哥千金贵体,自然戴不得这些东西,是小弟欠考虑了。”
正当他回身要将那傩面挂回去时,谢渠动了。
杞瑶手上一轻,是谢渠轻飘飘将那傩面接了去,动作十分优美地覆在了脸上。
“只给你看,又有何妨?”
说罢,他扔下一锭银子给小摊,自己拉上杞瑶施施然走了。
琳琅满目的彩灯,熙熙攘攘的人潮,拌嘴逗趣的怨人佳偶,一瞬间都变得很远了。
杞瑶仿佛听见耳畔呼啸而来的风,与环绕周身的夏意,密不透风,几乎要将他包裹,他能凝神的,不过是这双藏在傩面後的眼,他能为之驻足的,只有天地间一个谢渠罢了。
也是在同时,他骤然生出了一种快要流泪的错觉,天大地大,这一刹,他分明能感觉到谢渠的爱意,那是与天地间馀下的万物都截然不同的东西,可那感觉转瞬即逝,杞瑶不由得疑心起是自己的错觉。
他想去河畔买一盏莲灯,听人说放莲灯求愿很是灵验,杞瑶心想,若他去放,定要买下两盏,一只问问皇天,谢渠究竟是不是也喜欢他,一只问问厚土,这份惊世骇俗的情,他究竟说是不说。
回去的路上,杞瑶始终攀着谢渠的半边身体,而在他目光之外,谢渠始终借着傩面的遮挡,正大光明地看向杞瑶的脸。
看他温柔的眉眼与脸庞,妄图要将眉心的红痣刻在自己心里,永不会忘记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