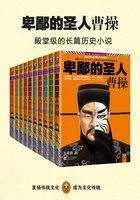书蛋文学>枕流光 > 第11章 十一 面圣(第2页)
第11章 十一 面圣(第2页)
两人各怀心思,杞瑶在暗中无意识摸了摸脸,谢渠则将手缩回袖中,看似随意地拈了拈。
二人到得殿中,谢灵泽正在批折子。
今日她穿了一身便服,黑色外衣里搭一件浅藕粉的衫子,恰好露出一截粉色的衣襟,衬得整个人明快鲜活不少,花容月貌,英气十足,不似那日在大殿上的不近人情。
“玉瑶,来了?”
杞瑶许久未被人这样唤过表字,一时亲近之意又平添几分,他跪下行礼,谢灵泽挥挥手让他起来:“私下里不必多礼,过来坐吧。”
谢渠却跟在杞瑶身後,一并掀了帘子过去,恭敬道:
“姑母,我也来了。”
“今岁开春我赠你的那匹西域马养得如何?”
谢渠边自觉拎起桌上的小炉开始煮茶,边回答道:
“尚且可以,苜蓿草吃得不错,但麸皮豆饼尤其难喂,我日日亲自拿了番麦去逗他,才勉强喂得下去。”
谢灵泽笑道:“那便是了,据说此类马性子烈得很,跑起来却是一等一的快,人送美称千里神驹,”她喊住谢渠,“喂,小凼儿,今年秋猎可有信心胜我?”
谢渠不服:“若去年不是我那匹马半路被绊了脚,早该胜你一筹了。”
“所以我才命人将那神驹送了你,”谢灵泽眨眨眼,“往後便是我不上场,也再无人可赢得了你。”
谢渠忙打住她的话:
“好了,扯那麽远做甚,今日是杞大人有事要说,我不过是个陪衬的。”
他将茶分与谢灵泽与杞瑶,自己直身坐着,再不作声了。
杞瑶听这姑侄二人说话听得有趣,先前他以为皇家麽,总逃不过兄友弟恭,父慈子孝,哪怕私下里早闹得不可开交,面子上总得做出一副恭敬模样。
可今日一见,他倒发现谢灵泽与谢渠更如两位无话不谈的挚友,个中情谊,委实令人艳羡。
“玉瑶,可是案子有进展了?”
杞瑶见谢灵泽不打算避着谢渠,也就不再磨蹭,他整理了前因後果,从查案伊始说起,一直说到他们一行四人在皇城司的推论,最後他起身道:
“便是如此了,望陛下圣断。”
谢灵泽抿了口茶,杯口白烟蒸腾,她透过那层白雾望向谢渠:
“凼儿,你自己解释吧。”
谢渠不疾不徐放下杯盏,说道:
“东宫有嫌疑一事,我当真无法,杞大人所举的件件证据,我亦无力反驳。”
谁料下一秒谢渠话锋骤转,反问道:
“可我想问,杞大人的调查当真滴水不漏吗?”
杞瑶不明其意:“当真,臣早已将所有可疑之处一一排查,再往下的,暂且确是想不出来了,若假以时日……”
谢渠打断道:“我且问杞大人,可有亲自去现场看过?”
杞瑶一时犹如被掐了三寸,面色难看得很,室内品字格的木桌,翠玉的笔搁,谢灵泽长长的黑色衣摆拖下一截,落在地上,像一朵盛开的深色罂粟花,谢渠锐利如鹰的眼神则随时要将他看穿,琥珀色的瞳仁紧缩,一切的一切都在眼前放大,他指节微微颤抖,半晌未发一语。
是啊,怎麽就忘了这档子事!
当日他看了大理寺的卷宗,见记录里无甚异常便搁到一边去了,事後也只顾着往下查,竟是未想起去最初的现场去看看!
在为官一事上,杞瑶终归是太过稚嫩,无论行事或心计。
他沉默不言,谢渠也不恼,自己又道:
“这本是裁正司分内之事,杞大人连案子最基本的情况都未明了,又要我如何相信之後的推论没有差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