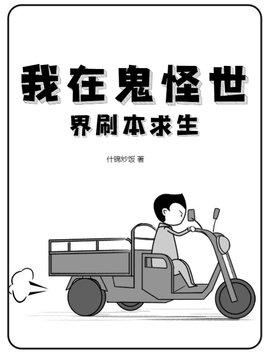书蛋文学>京雪未眠 > 第56章 暴雪夜 我弄脏的理应我来洗(第3页)
第56章 暴雪夜 我弄脏的理应我来洗(第3页)
的确不合适。
舒姥爷仍旧笑眯眯的,“只是想让你们年轻人之间相认,同我们这些长辈没关系,以後贺先生还是唤舒旭伯父。”
贺问洲气息依旧平稳,滴水不漏地应,“舒老,小瑾很聪明,性子也乖巧,谁见了都喜欢。不过我们之间的确不适合再添个兄妹的名号,我对她的好无需空名。您放心,不管是在京北,还是别处,只要我人还在,护她一辈子顺遂无忧。”
真情掺杂在随和的笑意里,犹如一记穿心的箭矢,将舒怀瑾牢牢钉在他身边。
面对这样一个成熟稳重丶矜贵斯文的男人,她很难不被他的魅力所折服。
舒宴清默然许久,“问洲,你最好做到。”
贺问洲的眸光慢慢踱过来,将舒怀瑾罩住,日落後的蓝调天空衬得他身形疏阔,眉眼愈发沉肃清和。浮世纷扰不过尔尔,他此生唯一所愿,仅她一人而已。
“这是我给小瑾的承诺。”
不管端的是什麽身份,有没有兄妹的名号,舒怀瑾能够得到这样一位位高权重的贵人守护,舒家长辈们自然满心欣慰。
入睡之前,舒宴清特地来敲开舒怀瑾的门,神情严肃地警告,“你们在外面怎麽闹都不会有人说什麽,在家不行,给我收敛一点。要是贺问洲引诱你做什麽,记得给我打电话。”
舒怀瑾探出脚尖,小声反驳,“说得好像贺问洲是什麽大坏蛋一样。”
“男人没你想得那麽好。”舒宴清恨铁不成钢,“不管这个人是谁,不管他拥有什麽身份地位,你都要有所保留,不能一门心思的扎进去。”
又是他那套爱要克制的理论,舒怀瑾耳朵听出了茧子。
“我知道的,哥,你不用再三强调啦。”
舒宴清:“知道归知道,你得切实履行。”
“好好好。”舒怀瑾敷衍着,忽然起了八卦的兴致。
“我记得阮阮还说你像个木头来着。是不是男人动心前後,都有两幅面孔?哥,你也是吗?”
“好端端的,扯到我做什麽?”
提到苏阮,舒宴清面色不太自然。最近困扰他的事不止舒怀瑾,还有对他发起猛烈进攻的苏阮。他就不该轻信苏阮的鬼话,真赴了她的约,到头来被她言语调戏,肢体上占便宜。他真是想不明白,以前看起来挺文静的一个女孩,怎麽忽然多了这麽多手段,踩在他濒临溃败的点上反复推拉。
舒宴清从没碰到过这样的事,步步退让,结果把自己绕了进去,剪不断,理还乱。
他不欲深想,言简意赅,“多的我不说了,免得你嫌我啰嗦。早点休息。对了,贺问洲最近自顾不暇,你少在明面上和他接触,等几个洲的发言拉票环节结束後,再观望整体情况。”
舒怀瑾耳尖,一下子猜到跟贺问洲那晚的举动有关,捺不住好奇心,“怎麽还和政客有关系?贺问洲要改国籍?”
“这些事你知道的越少越安全。”
“哈?有这麽夸张吗?”舒怀瑾说,“又不是在拍电影。”
舒宴清:“现实永远比电影荒谬。别看咱们关起门来岁月静好,外面全是恨不得一口扑上来分食的豺狼虎豹。尤其是资本和政客牵扯的国际金融犯罪案,通过各种不合理的长臂管辖抓捕,判处你终身监禁,保释金高达百亿丶万亿,说什麽你有钱,都是笑话,杠杆千百倍往上加,验钞机来了也没用。不然你以为贺问洲为什麽要随身带保镖?”
舒怀瑾似懂非懂,“他赚的钱不干净?”
“不是钱不干净,是人不干净。”舒宴清说,“他再干净,也没办法保证合作夥伴干净。这世上能有几个人盼着你好?不都是表面巴结,背地里恨不得将你拽下地狱。钱权这东西,要麽一直保持野心在上面待着,要麽,跌下来後,就别想再回去。”
同她讲这些已是越线,舒宴清及时中止话题,“这件事很复杂,不过他能处理好,你就安心待着,别捣乱。”
舒怀瑾心底藏着小九九,安静地应了声。脑子里还在琢磨思忖。
舒宴清口中的世界像一个诡谲危险的末世,悬在头顶的达摩克斯之剑随时可能落下。正所谓高处不胜寒,她只看到了贺问洲风光倨傲的一面,全然不知晓坐在这个位置,要面临多少危险。难怪他最开始面对她的撩拨,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後退。
归根究底,还是她阅历不够,看问题少了全瞻性。
她的确没什麽能够帮得上贺问洲的。
在床上翻来覆去半晌,她忽然生出一股雄心壮志,想为贺问洲做些什麽。
夜深人静之际,舒怀瑾脱了鞋,蹑手蹑脚地扣响客房门。
屋内一片漆黑,走廊的暗黄光影沿着木地板投射进去,映在男人漆暗的瞳眸里,平日里精心收敛的锋芒尽数溢出,同他对视的一瞬间,舒怀瑾隐约有种被野兽盯住的错觉。
从光线稍亮的地方过渡到暗处,舒怀瑾还没能适应过来,身体微不可闻地颤了下。
贺问洲禁锢在她腰间的臂膀紧实有力,薄唇覆上来,磁性好听的气音格外性感。
“脏了的内。裤带过来没?”
舒怀瑾被他突如其来的吻得双腿泛软,鼻腔溢出丝丝舒服的呜咽,不解道:“没有,你要我的脏衣服干嘛?”
他这个人身上的气质矛盾而和谐,既暴烈又温柔,将仅有的限定缱绻悉数赠予了她。哪怕是在恶劣环境中厮杀的猛兽,亦有柔和的部分,她何其幸运,独享了这份柔情。
她紧贴在他胸膛,清晰地感受到了他心脏震动的频率,一声又一声,鼓噪地压着耳膜。
贺问洲抚摸她的耳垂,像在把玩一件爱不释手的宝贝,“我弄脏的,理应我来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