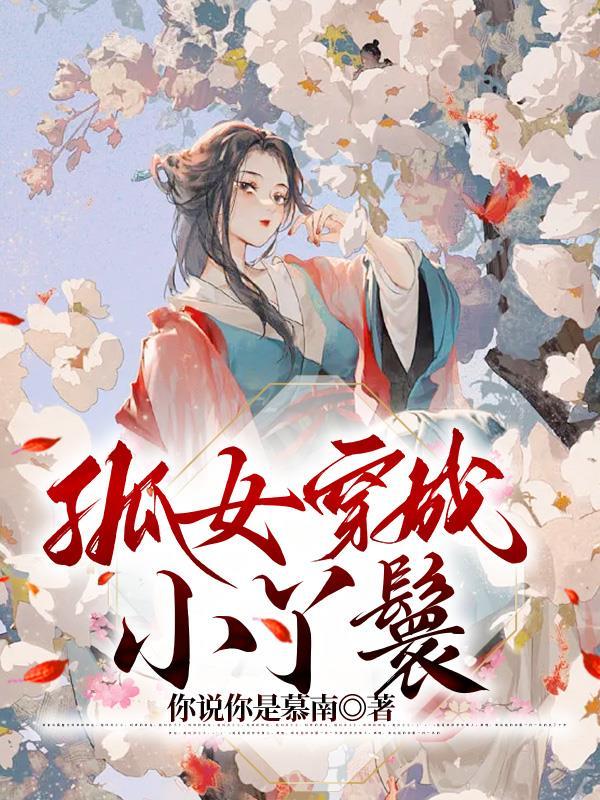书蛋文学>重回高考当状元 > 煤矿生活 二(第2页)
煤矿生活 二(第2页)
有些家境好的,书皮上印着卡通、英文字母、日漫人物,还有配套笔袋。
王昭手头有一张带“heokitty”浮雕的英文书皮,结果被刘小利当众调侃:
“哎哟,这不是昭昭小公主的专属书皮嘛?值了值了!”
整个上午,教室里“咔咔”剪纸声、“嗖嗖”涂胶水声、“撕书角”声此起彼伏,还有那一阵阵笑闹、抢订书的小混乱。
“喂,我的地理怎么少了一本?”
“给我点双面胶!我的书都糊住了!”
“谁把我英语书拿走了啊?!!!”
乔伊坐在最后一排,安静地翻着物理课本,指尖划过那张“第一课:光的干涉实验图”。
她轻轻合上书本,嘴角浮出一丝淡笑:
“这世界,还是需要‘课本’的。”
因为书是线性的,命运不是。
但书能让人从混乱中看见一页一页的秩序。
桐山二中是典型的o年代重点中学:
教学楼是浅灰色水泥墙,窗框是绿色铁皮;
操场是土操场,旁边竖着两根脱漆的旗杆;
校园广播总在上午o点、下午点放《卡农》《同桌的你》;
教师办公室飘着茶叶水、艾叶膏和粉笔灰的味道;
校医室里是风油精、云南白药和“体温表+红药水”的标准配置。
开学第一天的晚自习,格外安静。
每个人都有点累,也都有点新学期的紧张——哪怕他们曾刚从三号井前“准备挑战宇宙系统”。
可现在,他们只是普通学生,穿着校服、背着新书包、在傍晚的晚霞下,走进一个叫“高三”的季节。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陈树坐在靠窗的位置,正反复看着新物理书最后一章《光电效应》。
王昭在英语书上写着笔记:“vocabuaryist”(词汇清单)。
张芳翻着数学练习册,嘴里小声念着:“第一题不会,第二题也……”
刘小利干脆在书皮上画上了Ω标志,对着乔伊眨眼:“嘿,我偷偷把Ω-画在了每一本书上,它就是我青春的代号。”
乔伊笑了。
张芳靠在讲台边帮班主任改人名册,眼神掠过每个熟悉又陌生的名字。
马星遥,依旧最沉默,笔记整齐,字像电子线路图。
他们都回来了。
回到这座水泥楼、这段清晰课表、这段充满粉笔和书香的时光。
青春里这场“新书”“包书皮”的旧仪式,值得他们把它认真走完一遍。
因为他们都知道:
“下次再新书时,
我们可能就不是现在的自己了。”
虽然刚过完开学季,气温还没完全转暖,但桐林商厦的滑冰场已经恢复了往日的热闹。灯光打在真冰面上,映出一层层淡蓝的反光,像倒映着某些遥远又模糊的青春残影。
胡静坐在她熟悉的“场控位”上,一边登记滑冰鞋的尺码,一边远远望着场上的人。
今天来滑冰的,大多是初高中生,还有几对情侣。
喇叭里正播放着王杰的《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不算动感,但旋律一响起,总让人忍不住叹口气。
她今天穿得特别简单——牛仔裤,红格衬衫,扎了个高马尾,手边泡着一杯廉价红茶。她看起来跟往常一模一样,可心里,却不再是那个“只管场子是否结冰”的胡静。
她脑子里断断续续浮现的,是三号井的信号,是马星遥戴手表时那种若有所思的神情,是乔伊在纸上画公式时下意识的咬唇,是王昭故意冷静的“没什么”后面藏着的疲惫……
她看似坐在这里,心却像没下车的旅客,还停在那趟叫“Ω”的列车上。
她低头看了眼手表——不,是滑冰场前台的挂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