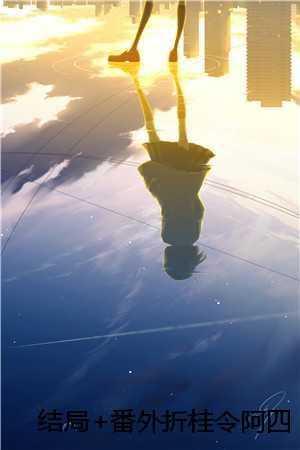书蛋文学>重回高考当状元 > 煤矿生活一(第3页)
煤矿生活一(第3页)
刘小利指着自家小时候住过的铁门:“你知道那时候最怕什么吗?不是没钱,是停电。”
乔磊边走边说:“我小时候烧水是拿煤块垒个三角架,锅放上面,水能烧半小时才开。”
乔伊走在最后,望着阳光洒在红砖墙上的纹理,鼻尖泛起一丝酸。
她不是这个时代的人,但此刻,她仿佛明白了一个词:
“有烟火气的生活,才能撑起人去面对未知的命运。”
他们每个人,在这一刻,不再是“行动组成员”,不再是“实验变量”。
他们是穿着矿服、走在旧砖路上的普通青年,
眼前,是时代的肌理;
背后,是一代人用煤灰和笑声筑起来的小世界。
广播喇叭悬在巷子口的电线杆子顶端,头朝着主街,铁皮外壳已经被雨水和灰尘侵蚀得白,底部挂着几缕掉线的黑胶布。平时它静静地在那儿趴着,像一个沉默的哨兵。
可只要每天傍晚五点半一到,不管阳光多斜、锅碗瓢盆多响,它就会突然被“唤醒”。
“滋啦——咔哒!”
铁喇叭里先是一声电流声,然后传出那个熟悉的磁带播放的前奏——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
“慢慢地绽放他留给我的情怀…”?是孟庭苇的《羞答答的玫瑰》。
这歌一响,全矿区的人都知道:“该做饭的做饭,该回家的回家。”
街口的小卖部,本来几个孩子正在抢跳棋,老板娘一听音乐响了,立马把塑料帘子拉一半:“别闹了,回家吃饭去!”
洗煤车间的大门前,工人还在换工作服,一边哼着歌一边拍身上的煤灰,有人朝楼上的窗户喊: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老范你媳妇儿的歌儿又响了!快下来接锅!”
老范一边笑一边系围裙跑出来。
整个生活区,仿佛在这一刻,有了节奏。
不是军号,不是铃铛,而是音乐。
每个大院的屋顶上都冒起了炊烟,灶膛里烧着煤球炉子,锅上是铁皮盖子,盖子因为蒸汽“嗤嗤”响着。
女人们穿着围裙,撸起袖子剁蒜、擀面、炒菜,男人在院子里洗脸、烧水,有的还一手拎着暖瓶一手挠着头。
孩子们更不用说了。
广播一响,他们像打了呼哨,三三两两地从矿山边、废铁轨、老澡堂后头飞奔回来。
裤腿卷着、脸上是汗,嘴角还叼着半截甘蔗。有人边跑边喊:
“快回来!你妈要把你饭喂狗了!”
这句话听着吓人,但没人真会喂狗。那狗都不在家——也跟着一群孩子跑街串巷去了。
矿上的“家狗文化”是一种奇特的存在。
那些土狗没有狗牌、也不上链子,但每一只都知道自己是哪家的。白天到处串门、晚上准时回窝。
它们陪着孩子们一起滚铁圈、掰猪骨头、抢大锅饼,到了吃饭点,就蹲在小主人旁边,不叫不闹,只是静静看着那锅。
有一条黑狗叫“煤球”,眼神比人都通透。
每次广播一响,它就跑去敲自家厨房的门,一爪子一爪子敲得特别讲理。敲三下,不多不少。
而音乐,成了这些生活的背景底色。
《羞答答的玫瑰》不是爱情,是一种节奏感,是一种“矿区黄昏即将来临”的信号。
它让人慢下脚步,让孩子不再打闹,让妈妈心软,让爸爸把酒杯拿出来。
那时的生活简陋,却处处是人情。
家家户户炖的是白菜粉条、大锅烙饼、干煸豆角,锅里是油渍汤花,锅边贴着麦皮面饼,熟了泡,掀起来就是香。
矿区里有个传说:听见孟庭苇的歌响起,空气里的香味就会浓三分。
吃饭时是全区最安静的时刻。
只听见锅铲敲碗、炊烟扑打窗户、电视机放的《新闻联播》主题曲。
屋里屋外灯光亮起,昏黄但柔和,像这个时代的感情:温吞,却让人安心。
饭后,家家出门散步。
老人坐在巷口纳鞋底,女人三三两两边走边聊,男人掏出烟来一根一根地递。
孩子们拿着矿区的冰棍,围着井盖玩跳格子。
喜欢重回高考当状元请大家收藏:dududu重回高考当状元小说网更新度全网最快。

![(综英美同人)[综英美]被毛茸茸包围的我今天也在努力养家+番外](/img/23458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