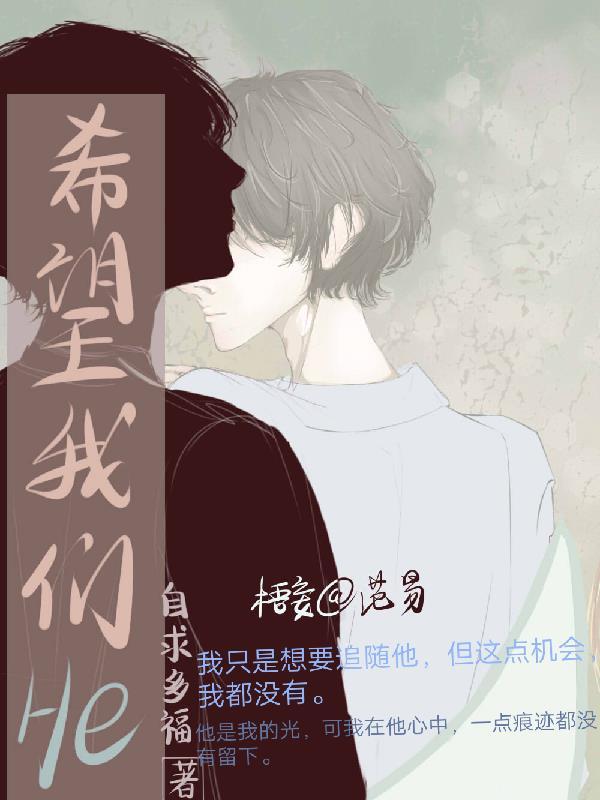书蛋文学>疆栩江栩贺容疆 > 第5章(第1页)
第5章(第1页)
>
我不敢回应。
我是谁?我只是江栩,一个卑微如尘土的奴婢。
他是谁?他是贺家的天之骄子,是未来要驰骋沙场、光耀门楣的大将军。
云与泥的差别,从来都不是说说而已。
我只能再一次选择逃避,装作没有听见,仓皇地挣脱他的手,将这个沉重得让我无法呼吸的话题,丢弃在浓稠的夜色里。
为了给他治伤,我几乎花光了在酒楼做工攒下的所有积蓄,甚至还向刻薄的房东婆子和酒楼的掌柜预支了工钱,欠下了一屁股债。
镇上的几个大夫都来看过,看过之后无一不是摇头叹息,说他的腿骨碎得太彻底,经脉尽断,已是回天乏术。而眼睛里的毒素更是奇特,他们行医多年,闻所未闻,根本无从下手。
我不信邪,我不信我拼了命从乱葬岗里拖出来的人,就要这样废一辈子。我像着了魔一样,四处向人打听,哪怕只有一丝一毫的希望,我也不愿放弃。
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让我打听到了一位奇人——叶承。
镇上的人说,他曾是京城皇宫里的御医,医术超凡,不知后来为何得罪了宫中的权贵,被贬斥到了这鸟不拉屎的边陲之地。
我揣着身上最后一点铜板,又厚着脸皮向酒楼掌柜借了一笔钱,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背着贺容疆,找到了叶承的医馆。
叶承是个看起来不过三十出头的男子,一身青衫,气质温润如玉,眉眼间总是带着一种悲天悯人的柔和。
他为贺容疆仔细诊治过后,那双温和的眉毛也紧紧地锁了起来。
“腿骨虽碎,但尚有接续的可能,只是过程会异常痛苦,非大毅力者不能承受。至于这眼睛……此毒阴狠,我从未见过,只能姑且一试,用金针渡穴之法,辅以汤药,看看能否将毒素慢慢逼出体外。”
有救!
这两个字,对我来说,不啻于天籁之音。
我再也控制不住情绪,“扑通”一声,直直地跪在了叶承面前:“叶大夫,求求您,求您一定要救救我相公!无论要花多少钱,无论要受多少苦,我们都愿意!”
叶承连忙将我扶起,温和地说道:“姑娘快快请起。医者父母心,救死扶伤乃是我的本分,我自会竭尽全力。只是……这治疗所需的药材,大多十分珍贵,花费……恐怕不菲。”
我咬了咬牙,眼神坚定:“钱的事情,我来想办法!”
从那天起,我活得更像一个高速旋转的陀螺,不敢有片刻停歇。
白天在酒楼的后厨烟熏火燎,晚上就去镇上的大户人家接些浆洗缝补的活计,一双手终日泡在冰冷的皂水里,很快就变得又红又肿,布满了裂口和老茧。
我将攒下的每一个铜板,都悉数送去了叶承的医馆,换回一包包苦涩的汤药。
叶承是个真正的好人,他知道我们拮据,时常会多送我一些处理外伤的伤药,有时候还会提着一个食盒来到我们那个破旧的家,笑着说是“做了些小菜,想请二位品尝品尝我的手艺”。
他会陪着贺容疆说话,聊一些京城早已物是人非的旧闻,聊一些兵法韬略,战事布局。
起初,贺容疆对他充满了毫不掩饰的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