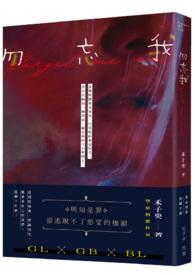书蛋文学>虐文女主,但痛觉转移 > 4050(第14页)
4050(第14页)
只偶尔看到谢昭昭满手的伤痕,赵晛心底才会浮动出一丝怜惜和愧疚感。但开弓没有回头箭,他不愿自己心软耽搁了薛蔓治病,后来索性就不再亲自割肉放血。
直到此时此刻谢昭昭突然将此事问出口,像是猛地撕开了他道德和尊严的遮羞布,令他脸色微微臊红,一时间有些不知该如何回答。
他崇尚儒道,以仁爱、礼义为立身之本,将君子之风刻进骨血,世人皆道当今太子渊渟岳峙,玉洁松贞。
而这样的他,却对一个弱女子机关算尽,不惜以名节和姻缘为束缚,画地为牢将她囚。禁。
赵晛几乎不敢对视她的眼睛。
他垂下首,似是想用长久的沉默将此事糊弄过去,但谢昭昭却不给他这个机会,他不说话,她便极有耐性地等待着。
殿内空气似是变得焦灼而窒息。
赵晛绷紧了面皮,半晌从唇齿间吐出一声叹息:“阿昭,我如今是真心喜欢你。”
当真是一句避重就轻的回答。
谢昭昭却不揭穿他的龌龊,她适当沉默了一瞬,低声道:“可是殿下,你也同样真心喜欢我表姐。”
赵晛僵了僵。
“殿下在我心中是明月高山般的存在,我自知配不上殿下,却还是抵不住仰慕殿下的心意嫁入了东宫。我不希望殿下因流言蜚语而误解我,更不想我们在一起是为了向旁人澄清真相,我想要等到殿下纯粹的爱。”
谢昭昭叽里咕噜说了一大段酸溜溜的情话,虽然没一句实话却说得面不改色,直将赵晛听得一愣一愣。
那明月高山的大高帽子扣在赵晛头上,他便是此刻有再多的想法和心思,也只能先咽回肚子里。
赵晛抿着唇,在心里挣扎了两下,还是忍不住道:“我自是相信阿昭,但父皇向来肆意惯了,从不将世俗规矩礼法放在眼里,我怕父皇……”
话还未说完,重喜躬身进了大吉殿。
他身旁带着一个端着汤药瓷碗的小太监,站定在两人面前:“娘娘,这是任太医给您煎,煎好的退热药。”
谢昭昭借机抽出手,将黏腻的掌心贴在衣裙上擦了两下,抬手接过小太监递来的药碗:“多谢两位公公。”
她装模作样喝了两口,见重喜还不离开,不由抬眸:“重喜公公,还有旁的事吗?”
重喜迟疑了一瞬,开口道:“陛下口谕,如今怪疾已愈,着令太子和太子妃,即,即刻收拾行幐离宫。”
谢昭昭:“……”
赵瞿什么意思?让她收拾行李滚蛋?
她又怎么惹到他了,他为什么在此时让她和赵晛离宫?
难道就因为她方才借着赵晛生辰打探橙昭仪的事情?
赵瞿的心眼当真是比芝麻粒还小,连一个解释的机会都不给她,一醒过来就急着让她离开。
谢昭昭心情颇有些复杂,却还不能表现出来,等送走了重喜,她看向赵晛:“殿下现在可相信我的话了?”
赵晛又忍不住红了脸。
宫里那谣言传的有鼻子有眼,他再一联想先前赵瞿对谢昭昭的特殊照顾,自然难免误会。
人一旦先入为主,那些回忆中的细节似乎都被添了层偏见。
可如今看来,他不但误会了谢昭昭,也同样了误会了赵瞿。
想必赵瞿突然叫他们收拾东西离宫,或许是听闻了那宫中的谣传,大抵觉得匪夷所思,便选择了最直接的证明方式。
——只要谢昭昭跟赵晛回了东宫,往后不在皇宫里侍奉了,谣言自然不攻而破。
便是退一步讲,赵瞿曾经对谢昭昭有过什么想法,但他并未付诸行动,如今也算是表明态度,及时将错误扼杀在了摇篮里。
至于赵瞿宠幸了模仿谢昭昭的吕昭仪,或许他就是喜欢这种素衣美人,总归赵瞿只要不将主意打到谢昭昭身上便是。
赵晛默了半晌,还是向她低了头:“阿昭,对不住,我不该疑心你。圆房的事情不着急,我愿意等着你。”
谢昭昭得到了满意的答复,却并不满意这个结果。
若是她就这样离开了,往后再想见赵瞿就难了吧?
她怎么也该向他解释清楚误会再离开。
谢昭昭吩咐雾面去收拾行囊,自己则在赵晛不注意的空档溜去了立政殿。她去之间在心底演练了无数遍该怎样解释,但到了殿外却被重喜拦住:“娘娘请回,陛下今日已经歇下了。”
谢昭昭瞥了一眼西边还未落下的太阳。
天还没黑,赵瞿就睡了?
这分明是挡她的借口。
早知如此她方才就不该离开立政殿,便守在他身边等着他醒来,也免得他这样记恨在心。
谢昭昭回了大吉殿,又在殿内磨磨蹭蹭拖延了大半个时辰,也没等到赵瞿改变主意,只好带着行囊离开了皇宫。
东宫与皇宫相隔并不算远,两座建筑物紧紧相邻,却被中间横亘的宫墙隔绝为了两个世界。
橙梓随同谢昭昭和赵晛一起回了东宫,等踏入宜秋宫,她敞开双臂,深吸了一口气。
“这些天快憋死我了,我终于自由了!”
橙梓小跑进了偏殿,换了身窄袖短胯的袍衫,提剑便一通挥砍,直到满身湿汗这才停手。
而谢昭昭便坐在院中石椅上,支着下巴不知在想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