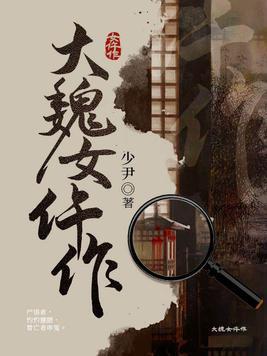书蛋文学>御前心理师 > 第422章(第2页)
第422章(第2页)
“人没了,屋子就塌得快,”李一如叹道,“我太爷爷以前也是这么说的,屋子只要还有人住,有一股人气撑着,就能住上好些年。”
柏灵默默听着,推开了手边的一道门。
这间院子从外面看起来和她从前的小家很像,只是篱笆累得更高些。
然而才一推门,柏灵就放弃了再进屋搜寻物件的打算——院子里摊着两架人的白骨,另一架在地上,另一架半掩在土中。
柏灵退了出来,看向牧成,“……我们还是走吧,这里,我觉得不可能还能剩什么粮食。”
“嗯。”牧成点了点头,他去到的几户人家,米缸也都是空的。
应该都是饿死的。
只是在今日以前,对于“饥荒”,柏灵还未有过这样的惨烈的认识。
过去在平京,她也曾听到过北边饥荒的消息——不管是平京还是越州,自建熙四十五年以后,都有大批的流民涌入。
史书上,也曾有许多“岁疫,十室九空”“大饥,人相食”的记载。
她脑海中忽然浮现出某种景象,仿佛就在过去的某一段时间里——或许就是她在百花涯与诸多贵人对饮谈笑的某个夜晚,就在同一片天空下,成千上万的饥民和难民正怀着恐惧和饥馑往南逃窜。
只要游过那条隔断南北的见安江,就能活下去。
而未能南下的百姓,大约就永远地留在了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柏灵觉得喉中一片苦涩。
这样的情形,在北巡的时候陈翊琮也见过么?
他应该也见过了吧……
柏灵下颌微微颤,她忽然觉得世上事未免太过残酷——她站在今天的江北往前回溯,很快就看到了更多往昔流民的命运。
即便是撑过了这条见安江,继续往南就一定安全了么?
不……倘使他幸运,停在了江洲,越州,停在了楚州或是去了平京,那或许确实可以暂时安居。
倘使一路南下,去了徽州呢?
且在平京时,建熙帝尚且能为捉出金贼细作而暗自舍数千流民的性命,放去别处,又会是怎样的情形?
柏灵不敢细想。
有些事原就不能细想,一旦细想,便都是眼泪。
“平原的村子应该是没有人了,”李一如轻声道,“还记得昨天那个婆婆的话吗,现在他们应该都在山上,但这一片的山离官道都远得很,如果我们要去投宿,估计还要耽误不少时间。”
“不进山了。”牧成低声道,对于江北的情形,他显然也预估错了,“我们还是走官道,如果路上再遇到商队,就再借搭他们的马车吧。”
“嗯。”柏灵和李一如都点了点头。
沉默中,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想起了江洲诚外,那批要高价带客北去的涿州商队。
现在想来,商队当时的要价或许并不算离谱,只是他们当时不明白。
第三十六章故地石碑
几人排查再三,最终还是决定离开这里。
在临近村口的地方,几人看见了一处孤立的石碑,石碑的正面已经被风沙侵蚀,许多字迹已经模糊不清,柏灵从一旁捡来几片树叶,用力刮下了几块附着其上的土块。
牧成和李一如也走近来看。
看起来,这似乎是这里最后的墓志铭。
雕碑的工匠是从抚州一路逃荒至此的难民,年逾古稀,且离开涿州之后日日咯血,自知时日无多,不愿做家中的拖累,便弃了渡江的念头,主动在这江北的“小贾村”留了下来。
在他来到这里时,这间村子已经空了,只有同样从北往南逃荒、避战的饥民会短暂地在此借宿,次日黎明又起,渡江南下。
“自抚州南下,往来千里,目之所见皆鹄面鸩形,耳之所闻无非男啼女哭。
“冬令北风怒号,林谷冰冻,一日再食,尚不能御寒,彻旦久饥,更复何以度活?甚至枯骨塞途,绕车而过,残喘呼救,望地而僵,每日饿毙者,何止千人……”
几人越往后看,越觉物伤其类,悲从中来。
孩童被弃于道途之间,或是被扔进沟渠之中,一旦饿死便被分食其肉,又或像买卖牛羊一样宰杀。
有恶徒将人哄至寂静无人处动手杀之,或是自己食用,或是放出买卖;有妇人枕靠在死人的身上,生啖其肉;还有人将饿死的人悬挂在富贵之家的门口,或是割下他们的头颅来向高门讨要一口食粮……
凡此种种骇人听闻的事情,在老人南下的途中层出不穷。
“被灾之初,不过贫穷下户,本乏盖藏,无以自给,或变卖衣物器具,或拆售房屋瓦木。及至搜刮殆尽,不得不逃亡四出。扶老携幼,号泣中途,带病忍饥,踉跄载道;
“乃未几而中户之家,日食不继,亦复如此矣;
“又未几而小康殷实之家,坐食山空,皆复如此矣。
“悲夫……”
再之后,字迹已与黄沙混为一处,再不能辨了。
三人静默地站在石碑之前。
村中白骨累累,不知哪一堆是曾经的雕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