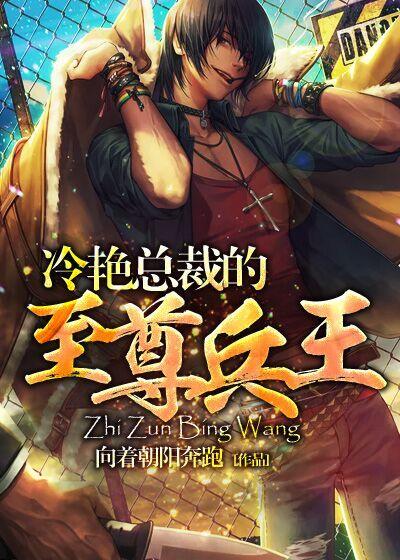书蛋文学>男主总想和我贴贴[穿书]+番外 > 第429章(第1页)
第429章(第1页)
月影堕入眸中的刹那,妖想起?了自己的名字,与名字有关的过往随之闪现,走?马灯一般,最?后停在了绘有小羊羔的那一面上。
姜冬至怔了片刻,缓慢地?抬眼,目光贴着雪地?一寸寸地?挪动,落到区别于其他骨骼的小小骨架上。收容尸体的奇特瞳孔被黑漆漆的空洞取代,讨厌的雪积在?眼眶上,为白骨增添了少许凄凉。
很难想象这么一副森冷的骨架曾经架着那么柔软的小小身躯。
姜冬至慌不择路地逃走了。
他摔在?雪地?里,扭了脚,不?管不?顾地?爬起?来继续狂奔。可是要跑到哪里去?他不?知道,哪里都没他的容身之处,但又不?能停下?,停下?会被藏在?雪里的绝望拖入万劫不?复之地?。
雪花像刮骨刀,一片一片地?刮下?皮肤,沉重的□□慢慢瓦解,更为沉重的罪孽露了出来,如跗骨之蛆,牢牢地?、牢牢地?攀附在?脆弱的灵魂上。
穿过树林后,大到可怕的明月映入眼帘,皎洁的银光像薄纱一般,一层一层地?压到姜冬至身上,很快就压垮了瘦削的脊梁。他被绝望抓住了脚踝,重重摔到雪地?上。没用?的,无论逃到哪里都会被月亮抓到,它一直在?盯着他,他逃不?掉的。
姜冬至哭丧着脸坐起?来,发现自己在?溪边,砸开冰面,将手探进去用?力搓洗。血,好?多血,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血。他的手好?脏,怎么就洗不?掉呢?怎么就洗不?掉呢!
姜冬至发出一声尖叫,垂下?头,用?血淋淋的手盖住脸,伏在?地?上痛哭起?来。
他到底做了些什么啊?明明知道靠近人类会给他们带来不?幸,为什么要下?山?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地?在?山上待着?不?就是没人说话吗?不?就是没东西吃吗?有什么忍不?了的?
手放在?抖动的后背上,绝望顺着手臂传到体内,好?像要把五脏六腑搅碎了。洛雪烟感觉自己张嘴时会呕出一颗流血不?止的心,然而并没有,姜冬至的名字从?嘴里流了出来,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她?听到自己哭了,俯身抱住受惊的孩子,想为他撑起?一片风雪进不?来的温暖空间。
“不?是你的错……”
姜冬至忽然感受到比小羊羔还要温暖的怀抱,像来自暖春的毯子,那么轻、那么轻地?盖到他身上。他抓住无形的手,因?柔软的温热感到战栗。绝望闭合了,他平静地?想道,不?会再好?起?来了。
那之后,姜冬至再没离开过山顶,变成了山的一部分。
幻听存在?的时间越来越长,可是他被绝望拔除了舌头,一个字也回不?了。除此之外,他的耳朵被绝望灌满,时不?时会听到悲戚的哭声,里面夹杂着小猫和小羊的叫声;他的双眼也被绝望荼毒,倒映在?其中的世界只有黑白二色,单调得可怕。
姜冬至无法确定?自己是否还活着。偶尔,麻木的身体会感到温暖的安抚,他疑心是那个死于冬至的男孩的幻觉,因?为实在?太过美好?了,像诞生在?春天的美梦。渐渐地?,他感觉不?到时间的流动了,就像时间之河底下?的卵石,日月从?身上流过,他沉默着抵达了永恒的彼岸,那里天寒地?冻,只有下?不?完的雪。
可是世间哪有什么永恒?
最?后一场暴雪降下?时,一名除妖师追着妖物来到了山顶,当着姜冬至的面斩杀了庞大的妖物。
洛雪烟读懂了血眸中的渴望,极力劝阻:“不?要出去!”
姜冬至没有听,跑到江善林面前,小心翼翼地?问出了令她?心碎的问题:“你,可以,杀了,我,吗?”
更为残忍的悲剧就此拉开帷幕。
那之后的一切顺理成章,姜冬至坐进了驶往栖净寺的马车里。他穿上合身的棉衣棉鞋,舒舒服服地?洗了个热水澡,还喝了好?多热粥,感觉自己好?像又变回了人类,临死前最?后的心愿了了,他很开心,每天都会笑。
可是幻听却很不?开心。
那个声音无时无刻不?在?劝他逃走?,好?几次甚至有了形体,拽着他的手腕往马车外面拖。
姜冬至因?此讨厌上自己的幻听和幻觉,它的反对让他觉得自己还贪恋着这条早该断绝的贱命,他为那个贪生怕死的自己感到羞耻。某一天,他忍无可忍,用?含糊的口齿和幻听艰难地?吵了一架,说了很多很多难听的话。没人比他更了解他的痛处在?哪,他这种吵法无异于亲手往心口上捅刀。
说了几句,姜冬至没觉得有什么,可是幻听哭了,哭得好?伤心:“不?要再说了。”
也许是因?为心脏太疼了,他幻想出温暖的拥抱,紧紧地?抱着自己。
姜冬至向幻听道歉,不?小心染上了哭腔:“对不?起?……”
棋试幻听终于消停了,那……
幻听终于消停了,那个声音不再劝姜冬至逃跑,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一如既往地和他说些俏皮话?。
姜冬至开始回应幻听了。他吐字温吞,说一句话?往往要组织好半天,可是幻听没有嫌弃他,每次都是等他说完才接话?,似乎是为了照顾他的情绪,它咬字也慢慢的,于是一场对话?变成了两只蜗牛的触角碰碰乐。
住进祠堂的那个夜晚,姜冬至抱膝坐在蒲团上,看着镀金的佛像,有些害怕。佛像的目光像月光,没有温度,冷冷地掷到身上,穿过透明?的心,过往的罪孽一览无?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