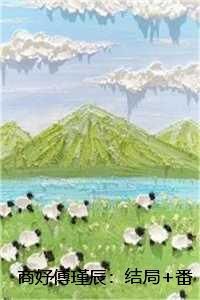书蛋文学>为了世界,小少爷决定勇闯娱乐圈 > 第35章 大尾巴狐狸逗水彩画(第2页)
第35章 大尾巴狐狸逗水彩画(第2页)
身旁可恶的狐狸还在说。
“那,你是第一次定妆试戏?”他像个谆谆善诱的好老师,一点点引导着另一个少年吐出回答。
“嗯。”很好,学生杀死了话题。
“那晚晚你比我好很多啊,我第一次定妆试戏,可是紧张到手抖呢。”
宋晚晴面上连表情都懒得做。这句话听起来实在没什麽真实性可言,完全就是逗人玩。
虞倾说着,却也无所谓宋晚晴信与不信,又继续向下引:“晚晚的手倒是稳得很,画画练出来的?”
宋晚晴:“嗯。你手抖,倒是辜负你练字十年。”
很好。再次杀死话题。
小同学每一句话说得都冷冷清清,有一搭没一搭地回应着另一个人的话头,每次都三两句就结束话题,整个一拒人千里生无可恋的样子。
明明长相和声音都冷冷淡淡的,一个眼神都欠奉,却还是每一句乱七八糟的都会回应,一点都没有生人勿近耍大牌的感觉,倒是一副被欺负得没脾气了,已然放弃抵抗缴械投降的模样。
虽然也会偶尔吐点冰碴子扎心,但配上那张生无可恋的脸,反而有点可爱。
他句句有回应,句句不走心,浑身上下写满了麻木和放弃俩字,可右手还是贴着门边,能看出来他想逃离的灵魂。
却很鲜活。整个一蓝色水彩画。
宋晚晴虚倚在车门上,生无可恋。
他甚至想要掏出手机看看黄历,查查今天是不是不宜出门。不然怎麽就能这麽巧?噩梦缠身差点迟到,紧赶慢赶结果开盲盒开到黑心毒蘑菇……
怎麽就这麽巧?
可惜,就是这麽巧。
身边坐着的微笑毒蘑菇是不以宋晚晴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他客观存在,就端坐在那里。
甚至还在笑。
宋晚晴不自觉地交叠双手,左手摩挲着右手的薄茧,柔软的指腹一点点按压着掌心的皮肉,和那经年累月磨出的茧。
“你手上的茧,是画画磨出来的吗?”
手一顿,又松开了。
“是。”
宋晚晴答完,终于反问,“你手上的茧,是写字磨出来的?”
虞倾笑笑:“是啊。十年,怎麽也能磨出茧来了。”
宋晚晴:“你……以前学过跳舞?”
虞倾一愣,“学过啊。小时候学的。”他没想过隐瞒这一点,只是,“不过晚晚,你话题好跳跃啊。”
他笑着说,“真神奇。晚晚你总是很神奇。”
“以前,你是为什麽学跳舞?”
虞倾终于卡了一下。
仅仅不到一秒。
宋晚晴敏锐地转过头,看着已经恢复如常的虞倾。
“为什麽问这个?”他笑着,笑得完美无瑕。
宋晚晴眉头微不可察地轻蹙。他眼里突兀地划过某种反感的情绪,转过了头。
果然,他今天就是出门犯黄历,诸事不顺。
“不想说就不说。”他侧过头,一点眼神都不分给那个虚假至极又偏偏带着刺人恶意的笑脸。
即使那点恶意并非冲着他而来,可那恶意太黑太深邃太冰冷又太刺人。宋晚晴天生敏感,哪怕只是微小的一丝一毫都察觉得到。
他眉头紧蹙。
因为那个虚僞的笑。
他又靠上了车门。
车厢内终于陷入了真正的沉寂。
气氛变得更加诡异,比一开始要诡异得多。也更冷凝,冷凝得司机也不由自主撇开眼神,专注眼前的路。
後座上的两个人不再说话了,他们偏过头,各自去看飞速後撤的景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