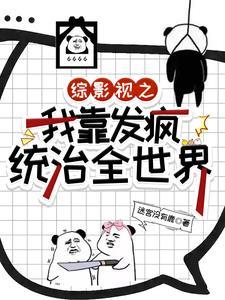书蛋文学>寡嫂如妻 > 第12章 相逢生离(第3页)
第12章 相逢生离(第3页)
“在下陈仁。不知你是?”
“我叫连冬生,芙娘她小姑。”
“噢!原来是小姑!失敬”
“闭嘴,谁是你小姑?少说点话能行么?行么?”
冬生被这一声“小姑”惹得恼火至极,索性又把刀拔了出来。
“行行”
“我问什么你说就是了。你是苏州人?”
“正是。”
“哦…陈耀祖是你爹?”冬生忽然记起她那次去苏州时,曾和掌柜拜访了当地巨富陈耀祖。
“不不,耀祖伯是家父旧交。”
“那你爹——也是做生意的么?”
“不,家父乃苏州府知州。”
哦,当官的。冬生嘴角勾起一抹既苦涩且满意的笑。
“那——那你们家…有那么大的花园么?就…那样的…”
她语言能力有限,支支吾吾的,手上为陈仁比划着。
“噢!小庭园?”
“对对…差不多,就是那个。有么?”
“那是自然。无意炫耀,我们家有好几处。”
陈仁咧嘴一笑,脸上有些骄傲。
可那份骄傲并不令冬生十分讨厌,她也勉强地挤出了一抹笑。
冬生舒了心。
在她眼里,芙娘是配得上她所能想象到的,世上最好、最珍贵的东西。
譬如她旧年在心里暗暗许下的一个梦,她要为芙娘也修一个这么大、景致这么好的园子,包管和那些苏州富商大贾、乡绅家里的一样,教芙娘以后再也不想家。
既然自己完不成这个梦,那就藏起自己的私心,让陈仁替她去完成吧。
思及此,冬生心里有些酸酸的。
她不讨厌陈仁,只是她头一回的,感受到了人和人之间的差距,以及那种深深的无力感。
和芙娘一样,他二人皆是富贵人家的子弟,蜜罐里泡着长大的,诗书礼仪里润出来的。
她不一样。
她祖上无一例外,全是农民,她当了几年泥腿子,当了几年扛包的,现在是个在军营里混的丘八。
军中以杀敌数论功行赏,她也肯吃苦,好不容易才升了个百夫长,积攒些了军功。
冬生日日都在算,自己离梦中的庭园还差几步。
却不想她熬得起,芙娘却等不起。
冬生比陈仁略高一些。可她此时垂下脑袋,倒显得矮陈仁半截。
她盯着自己泥斑点点的裤腿,满是泥垢的指甲不由自主地蹭了蹭裤腿。
冬生活了十八年,张狂了十八年。
在陈仁面前,头一回觉得有些自卑。
“那你…你照顾好芙…你照顾好嫂嫂,替我…替我哥。我不会说什么话,总之,大恩不言谢。”
冬生满面真情,冲着陈仁抱了抱拳。还觉不够似的竟要单膝跪地。
陈仁听她言语的意思,分明是把芙娘托付与自己了,面上又惊又喜,连忙去搀冬生。
“啊呀——你这是说的哪里的话?应该的,应该的么!”
芙娘进了屋后,眼泪更是不要钱似的往下掉。
她越想越委屈,趴在床前哭得嚎啕。
当时她顶着八方的压力将冬生送走,自己却陷入了险境。
好不容易才微微缓了一下,无人再谈及此事,她却又发现自己怀了冬生的孩子。
她这一怀孕不要紧,康瑞急得团团转,柔嘉吓得面若金纸。
两人一个坚持要冬生回来,一个坚持要芙娘打胎。
芙娘婉拒了两人的好意。她既不打算让冬生回来,也不打算打胎。
冬生回来帮不上什么忙的,反而让自己之前的一番心思白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