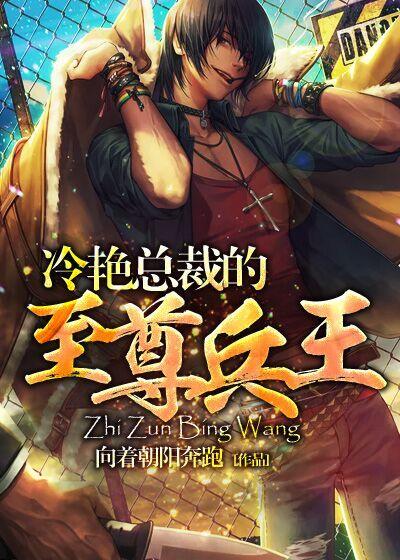书蛋文学>今天和林老师贴贴了吗+番外 > 第110章(第1页)
第110章(第1页)
万种风情都挂上了眉梢,堆叠在了眼角,天地间黯然失色,只剩那桃花眼底倒映出了世间万物,染上独属于那人的色彩。
安鱼信被不加掩饰的明媚容颜冲击得愣了半拍,片刻后回过神来,长吁一口气,摆摆手:“好汉不提当年勇。安某人现在就是个体育废物。”
“我感觉这么说很像说教,我不想这样。”林溪桥漫不经心地叠了个甲,胳膊肘撑在护栏上,手背虚虚抵着脑袋,歪头看她,“但确实该多动动。身体垮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好懒。”安鱼信摇摇头,“一点都动不了。”
林溪桥不说话了。
亭子外头的土地上铺了一层薄薄的落叶,又有一根树枝探头探脑地斜伸进来,叶子黄了一半。安鱼信正没事儿干似的盘着手边的叶子,便听林溪桥说:
“以后我带着你运动,运动到老,包你长命百岁。”
……又是这种听起来好像能够相伴一生的、过于亲近的话。
安鱼信不知怎的有些烦躁。方才蹦极时心底那股找不着门横冲直撞的气又开始蠢蠢欲动,叫嚣着划地盘,揪得心口一缩一缩,有些酸胀。
恰逢此时一阵风过,花果香往她身边飘了飘,和她本身的气味纠缠在了一起。林溪桥就在纠缠着的香气中转过了头,问她:
“好不好。”
声音很轻很柔,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像是笃定她会答应似的。
不好。
现在是现在,未来是未来。
风声中,安鱼信闭上了眼:
“你总是谈以后,会给我一种荒谬的错觉。”
“什么错觉?”林溪桥问。
安鱼信抿了抿唇,心一横。
她说:“你也喜欢我的错觉。”
安鱼信说完就合上嘴,不敢再看那人,只是侧头看着风中摇摆着的黄叶,和更远处树梢上一闪而过的小动物。
黄叶落下了一片,相伴而生的还有那破碎的、不甚清晰的“嗯”。
她想,或许是风声有点大,自己没听清。勉强平复下因着那个单音节语气词而狂跳的内心,她又问:
“你说什么?”
等待了许久,却再没有听到什么动静了。
——所以方才果然是自己听错了么?
些微的失望一点点上涌,她想着“果然如此,不必有什么过激的情绪”,正欲转过脑袋时,却听得身旁一声沉沉的“闭眼”。
不明所以,但她照做了。然后她感觉自己的下巴被轻轻捏住了,脑袋被掰着转了个方向。
唇上传来了温软的触感,一触即分。
风声中,那绵软的长发轻扫至她耳畔又被拨去了。她听见林溪桥说:
“嗯。”
“我喜欢你。”
声音近在耳畔。
风停了。
心如擂鼓,她睁开眸子,在愈演愈烈的怦然响动中对上了林溪桥招人的桃花眼。
瞳底只有自己。